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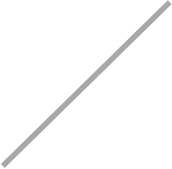
在我看来,所有人类知识中最有用却最不为人类了解的一点,就是对人类自己的认识 [卢梭注2] 。我敢说,仅仅那些镌刻在德尔菲斯神庙上的铭文,就比所有那些伦理学家的鸿篇巨制所蕴含的箴言显得更加重要,理解起来也更加困难。
因此,我将此篇论文涉及的主题视作哲学思考中最有趣的一个问题。
但是同时,不幸的是,对于我们而言,这也是哲学家们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我们如何在不了解人类的前提下去探讨人类的不平等?我们如何能够分清人类特征中哪些是其固有特征,哪些又是环境和进步在其原始状态基础上的增加或改变?这就像那海神格劳克斯Glaucus的雕像:时间、大海和暴风雨使它失去了原有的模样,使海神的形象看起来不再像一个神,而是像一头凶猛的野兽。这正如那人类灵魂在社会中扭曲的面孔,由于不断发生的上千种原因,在接受诸多知识与谬误的过程中,在身体构造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以及在情欲的不断冲击下,它早已改变了原有的样子,变得让我们几乎难以辨认了。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那些根据固定不变的准则行事的存在,不再是具有造物者赋予他们的卓越、崇高的简单的存在,而是自认为合理的情欲与处于错乱状态中的智慧的畸形对立。
更为不幸的是,正是 人类取得的所有进步使其不断远离最初状态 。我们获得越多的新知识,就越无法获得理解最重要事情的途径。也就是说,我们越是努力地去研究人类,就越无法理解人类。
很显然,我们应该从人类构造的一系列变化中去寻找将人类区分开来的差别的最初源头。这里存在着一个共识,即人类和其他所有物种一样,在最初状态下是平等的,直到不同的生理原因使一些物种发生一些可以被我们观察到的变化。事实上,对于这些最初的变化而言,无论它们以何种方式发生,都不可能同时在一个物种的所有个体上产生相同程度的影响,而是会出现有的人在获得不同品质后变得完善或者堕落——这些品质或好或坏,但都不属于他们的本性,而其他人则可以更长时间地保持在自然状态下的情况。这便是人类不平等的最初起源,这样大致的阐述比精确地考察其真正的原因要来得简单。
因此,希望读者们不要期待我能够明白那些在我看来如此难以理解的事物。我一开始做了些推论,然后尝试着做了一些推测,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旨在将之阐明,呈现出其真实状态。其他人可以轻易地沿着这条道路走得更远,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轻易地到达终点。这是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只需要理清人类现在的特征中哪些是最初的特征,哪些是非自然的特征,也不是只需要很好地去理解一个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过去可能从未存在,将来也可能永远不会存在的状态,尽管有关这一状态的精确概念将有助于我们对现存状态的研究。人们还需要更多哲理去想到一个试图精确定义在对这个主题进行可靠观察时所要注意的事项。在我看来,能够出色解答以下问题的人堪称我们这个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Pline
 ,这一问题是:为认识自然的人类,什么样的实验是必需的;以及在社会中,进行这些实验的方式有哪些?我并没有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而只是深入地思考了这一主题。我敢预言,无论是最伟大的哲学家还是最强大的执政者,都无法很好地从事这些实验。如果我们期待着他们双方共同协作,尤其是期待他们双方为了达到成功,肯以坚韧的精神或者无穷的智慧和必要的意愿共同协作,那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这一问题是:为认识自然的人类,什么样的实验是必需的;以及在社会中,进行这些实验的方式有哪些?我并没有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而只是深入地思考了这一主题。我敢预言,无论是最伟大的哲学家还是最强大的执政者,都无法很好地从事这些实验。如果我们期待着他们双方共同协作,尤其是期待他们双方为了达到成功,肯以坚韧的精神或者无穷的智慧和必要的意愿共同协作,那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人们至今还未对这些艰难的研究作深入思考,但这些研究却是我们得以了解人类社会真正基础的唯一途径,是让我们排除在这条道路上令我们望而却步的诸多困难的良方。正是对人类本性的无知使得我们对
自然法(le droit naturel)
 的定义模糊不清。正如布拉马基Burlamaqui
的定义模糊不清。正如布拉马基Burlamaqui
 所说:“法”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自然法”的概念,显然就是关于“人类本性”的概念。因此,正是从人类的这一本性出发,从人体的构造和状态出发,人们才得以推导出这门学科的准则。
所说:“法”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自然法”的概念,显然就是关于“人类本性”的概念。因此,正是从人类的这一本性出发,从人体的构造和状态出发,人们才得以推导出这门学科的准则。
当人们发现所有那些讨论过这一重要主题的作者,对这一点的理解都有所不同时,他们必定会感到惊讶和不解。在所有这些最具权威的作者中,我们几乎无法找到任何两个人拥有一致的观点。且不提那些古代的哲学家,他们似乎竭力要在最为基础的准则方面互相反驳。那些罗马的法学家们无情地将人类和其他所有动物毫无区别地置于相同的自然法之下,因为他们宁可把“自然法则”这一名词,理解为自然作用于自身的法则,而不是自然所规定的法则;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学家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理解“法则”这个词语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法则”只不过表示大自然为保证所有生命体的共同自我保存而在它们之间建立的一般关系。现代的法学家们却将“法则”这一词语理解为,对一个精神的存在,即一个具有理智和自由意志,而且在他与其他存在的关系中被尊重的一个存在所制定的规则。
因此,对于他们而言,自然法的权限必将仅仅局限于有理性的动物,即人类。但是,由于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来诠释这个法则,由于他们所有人都在如此形而上的准则基础上建立这套法则,以至于极少有人能够明白这些原理,更别说让自己发现这些原理了。
因此,尽管这些知识渊博的人所下的定义永远处于相互矛盾的状态,但却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除了那些伟大的推理爱好者或者深邃的形而上学者,没有人能够理解自然法,因而也无法遵守这个法则。也就是说,人类为了建立社会一定是使用了智慧的,这种智慧需要经历大量艰苦的努力才能被发展,而且即使在社会状态里,拥有这种智慧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的。
既然我们对大自然的了解如此肤浅,而且对“法则”的理解存在如此大的分歧,我们便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关于自然法的定义。因此,对于所有那些我们在课本上找到的定义,它们的缺陷不仅体现在其定义的不统一上面,而且还在于它们是从人类并非天生拥有的知识以及人类只有离开自然状态后才可能产生的优势概念中提炼出来的。人们往往先寻求一些能够促进公共利益而被大家共同认可的准则,然后将这些准则综合起来,便称之为自然法。这样做的唯一依据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准则的普遍实施中看到好处。毫无疑问,这是下定义的一种最简便的方式,同时也可以说是以武断态度来解释事物性质的最简便的方法。
但是,由于我们对自然人类根本一无所知,因此,我们想要确定自然人类后天获得的或者最适合其构造的法则也只是徒劳。有关这一法则,我们所能够明确指出的只有以下两点:首先,为了可以称其为法则,必须使其规范对象的意愿有意识地服从这个法则;其次,这个法则必须是自然的,能够直接体现自然的声音。
让我们将所有那些只能让我们看到人类既成模样的科学书籍扔到一边,仔细去思考人类灵魂最初、最简单的运作吧!
我从那里看到了先于理性存在的两大原则,其中一个原则让我们对自己的幸福(bien être)和自我保存产生浓厚的兴趣,而另一个原则就是在看到所有感性存在尤其是同类死亡或者痛苦时会产生天然的反感情绪。而我们的精神正在做的就是,在不需要引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sociabilité)的前提下,对这两个原则进行协调并且加以配合。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个原则的协调与配合催生了自然法的所有规则。随后,理性通过其不断的发展,终于达到了让本性窒息的程度,那时候,便不得不将这些规则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了。
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在将人类变成一个人之前先将他变成一个哲学家。他们并不仅仅因为后来出现的智慧和教训,才对别人存在义务。只要他不去抗拒怜悯心的自然冲动,他便永远不会对其他任何人,甚至是任何感性的存在作恶,除非是在他的自我保存受到威胁,他被迫优先考虑自己时,才会做出这样的正当举动。通过这一方式,我们也可以结束有关动物是否遵从自然法的古老争论。这是因为,很显然,动物在既没有智慧又没有理性的情况下是无法意识到这个规律的,但是由于它们拥有的感知与我们的天性有些共通之处,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它们也遵从自然法,同时,人类也被迫对这些动物存在某种义务。事实上,如果我被迫不对我的同类作恶,这更应该是因为他是一个感性的存在,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这个性质既然在畜牲和人类之间共通,那么它至少应该给予畜牲一种权利,即在对人类毫无益处的情况下,人类不应当虐待畜牲。
这个研究主要是关于最初的人类,关于他们的真正需求及他们义务中的主要原则。人们在探讨道德不平等这一政治主体的真正基础的起源,以及这一政治主体中成员相互间的义务,还有成千上万其他相似问题时会遇到重重困难,为了消除这些困难,这个研究是唯一好的途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至关重要而又有待阐明的。
当我们以一种平静、公正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时,一开始它似乎只展现出了强者的暴力和对弱者的压迫。一些人精神反抗所遭受的严酷,让人们对另一些人的盲目感到惋惜。由于在人类中,没有任何东西比由偶然而不是智慧产生的外部关系来得更加不稳定,因此,乍一看,人类的组成似乎是建立在一片片移动的沙子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称这个外部关系为强或弱,富裕或贫穷。
只有当进一步观察,剥去围绕在建筑物周围的沙尘时,我们才能够瞥见这幢建筑物不可动摇的根基,才能够学会尊重它的基础。然而,如果没有对人类、人类的自然禀赋以及他的持续发展的深入研究,我们永远无法做出这些区分,永远无法在事物的现有组成中将神意的东西与人类艺术产生的东西分离开来。我思考的这一重要问题引发的所有其他政治和道德推理对我的研究都非常有帮助,我所推测的政体历史对于人类而言绝对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一课。
当我们考虑到,如果任由我们自然发展,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就应该学会感激这个人:早在他用乐善好施之手改正我们的制度,并给予这一制度不可动摇的基础时,他便已经预测到了现行制度可能导致的骚乱,并用一些看起来似乎使我们遭遇无限苦难的方式,使幸福常与我们同在。
神让你做什么样的人?
现在,你在人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对此,你应该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