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义、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唯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徐爱说:“圣人著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像春秋五霸之后的事,圣人不想详细地给人们看,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也那么笼统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发生的事情淡而少,能记下来流传的就更少了,这是可以想见的。当时世风淳朴,大概没有华丽修辞、注重文饰的风气,全是淳厚朴素、全无文采的社会气象。这就太古的时代,非后世所能比拟。”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也要删掉它呢?”
先生说:“即使有流传下来的,也因为世道变化而不再适宜了。社会风气日益开放,文采日渐兴盛。到了周朝末年,就算想用夏商的风俗来改变,也是不可挽回了。何况伏羲、黄帝时的世风呢?又何况炎黄朝代呢?各朝代治世的表现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一个道。孔子效法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周文王、周武王时的制度也就是尧、舜时的道。只不过是因时而实施不同的政治。他们的设施政令,和其他时代自然不同,把夏、商的制度政令施行于周朝,已经不合时宜。所以,周公想并采禹、汤、文王的举措,碰到不合适的地方,还需夜以继日地深入研究。何况太古时的制度政令,难道还能实行吗?这正是孔子删略前代之事的原因。”
先生接着说:“专门从事无为而治,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因时机环境适宜而采取政治策略,而非要去实行远古的风俗,这是佛教、老庄的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社会进行治理,却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以道为本,而以功利之心来实行,这正是五霸以后治世的情形。后来的世儒们诸多人讲来讲去,其实只讲了个关于眼前功名利禄的一些术。”
先生又说:“唐虞以上的太平之世,后世不可能恢复,省略不谈它可以。尧舜禹三位贤君之后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仿效,可以把它删除。只有三位贤君执政之时的太平之世,是可以去借鉴实行的。然而,世上议论三代的人,对三代治理天下的根本视而不见,仅注意到一些细枝末节。如此一来,三代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不能恢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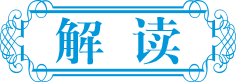
阳明先生认为,治国的制度要因时因地来制定,以使令顺民心,使之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所以,因时政治,是巩固统治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他又认为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在本质上它们遵循的仍是一个道。这个“道”,即是存天理,灭人欲,正人心,致良知。只有不变这个“道”,在政令制度中体现这个“道”,才可达到先王盛世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