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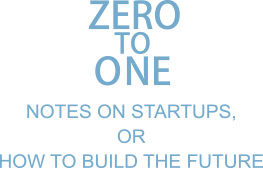
2014年11月上旬,我去爱尔兰参加了一个名为Web Summit的网络峰会活动。之所以不辞劳苦去那里,是因为邀请我的组织者说,他们安排了我跟彼得·蒂尔同台演讲。这么近距离地接触硅谷创投教父的机会,我岂能错过!
爱尔兰去是去了,但因为组织者的原因,我除了在舞台上远远地看着彼得·蒂尔演讲之外,跟他并无亲密接触。但我也并不遗憾,因为,彼得·蒂尔在我眼中已经超越了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精神和象征。他象征着美国异想天开、特立独行但又脚踏实地、从无到有的创新精神。这种人,如同乔布斯,死了依然活着,活着又何必着急见面?
随着PayPal的创办,彼得·蒂尔开始登上硅谷创新的舞台中央。在PayPal卖掉之后,他和他的同事们——包括埃隆·马斯克在内的人称“PayPal黑帮”的一群哥们儿,重新出发,做特斯拉的做特斯拉,办领英(LinkedIn)的办领英,而彼得·蒂尔选择做投资,创办了Founders Fund(创始人基金),开启了硅谷投资界的新格局。
彼得·蒂尔闯入硅谷投资界,本身就以一个颠覆者的形象出现。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对硅谷投资者的批评:“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我们需要能飞的汽车,但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符——指技术含量不高的推特。)他批评其他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为了谋求短期快速的利润,只敢投资轻量资本的创业,导致人类几十年以来在比特层面进步很大(互联网),但在原子层面进步很小(尖端科技)。他的标志性投资,做的是探索宇宙的火箭、取代人类的机器人、高层算法的人工智能、治疗癌症的药物、虚拟现实的沉浸设备等等。这里面有一些行业现在已经逐渐升温甚至炙手可热,但在当年彼得·蒂尔投资的时候是所有VC避之唯恐不及的重资产高风险行业。
有一个笑话说,如果你发现路上所有的车都在违规逆行,那大概是你自己开反了。而彼得·蒂尔就像这样一辆车,他不仅一往无前、无所畏惧地逆向而行,还让路上所有其他的车困惑和怀疑是不是自己开反了方向。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蒂尔的Founders Fund在硅谷资金规模并不是最大,历史也并非最长,但它的影响力却超越了国界与时代,直接照亮了世界与未来。
在彼得·蒂尔所有被人称道的重大决策里,最让我敬佩的是他创办了旨在鼓励高中和在校大学生休学创业的“20 under 20”项目。这个项目,每年选出20~25个20岁以下的青年天才,两年之内给他们10万美元去做他们自己最想做的创业项目。这个项目的官网上写着一句话:Some ideas can’t wait.(有些创意实在不能坐等!)——确实,假如比尔·盖茨或马克·扎克伯格等到从哈佛毕业再创业的话,人类就不会有微软和Facebook,或微软和Facebook就不是比尔和马克的了!
即使在美国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彼得·蒂尔推出的这个“20 under 20”项目还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人们指责这个项目鼓励学生追求商业成功而偏离学业。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默斯甚至说这是“10年来导向性最错误的慈善项目,它旨在贿赂学生抛弃学校教育”(I think the single most misdirected bit of philanthropy in this decade is Peter Thiel’s special program to bribe people to drop out of college)。
但是,这个项目成立4年来,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引发了同样巨大的积极反响。麻省理工学院(MIT)在项目成立之初就热烈祝贺它的两个学生入选,并鼓励他们想回来随时回来。彼得·蒂尔要证明的是:人们除了高等教育之外,还有其他的成功路径。
在该项目的网站首页,彼得·蒂尔引用马克·吐温的一句话来标明他的哲学:I have never let my schooling interfere with my education.(我从来没有让上学这件事干扰我的教育。)通过这个项目(后来改名为“蒂尔奖学金”),彼得·蒂尔向传统教育和人才观发起了挑战。可以想象,假以时日,从这个项目里必将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公司和著名的企业家,将在许多方面彻底改变人们对教育、对成长、对创业以及对人生的某些固有态度,推动社会更快速地进步,推动人生更自由地发展。彼得·蒂尔奉献给世界的,将不仅是一批伟大的公司和科技,还包括他这种站在人类发展高度来考虑问题的思想。
作为中国天使投资人,我密切关注着彼得·蒂尔的各种投资和言论,并获益匪浅。他的这本新书《从0到1》在国外出版前,我就有幸先睹为快,看到了朋友从美国寄来的英文文稿。中信出版社及时推出中文版,对中国投资人、创业者、政府机构、教育机构,都是一件令人喜悦和激动的事情,希望彼得·蒂尔的创投思想与实践被更多中国读者所熟知。我也一直在考虑,在中国推动成立一个类似“蒂尔奖学金”的项目——也许考虑到中国特色,这个项目必须改名为“22 under 22”(22岁是大学毕业的年龄),一个以应届毕业生为主的创业奖励项目,想来不会引发一个馒头之类的血案吧?
我以为我是一个思想领先的人……没想到,中国教育部在2014年11月颁布了支持大学生休学创业的政策。无论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彼得·蒂尔对青年人创业的强劲推动和支持,显然是这个波及全球的创业大合唱里最强劲的声音,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创业潮,鼓舞了无数中国青年创业者。
尽管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中国的创投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无奈的事实是:即使全球知名度已经相当高的阿里、腾讯、小米和京东,它们的产品在中国之外的用户依然微不足道。我在为彼得·蒂尔新书出版而高兴之时,不禁在想:中国何时才能诞生像Facebook、谷歌、苹果、特斯拉这样征服全球的公司和产品呢?
我希望这样的时刻早日到来。也许那个时候,彼得·蒂尔就会常常来中国参加各种网络峰会的活动。到时候,我会让部下给他发个请柬,说来中国吧,可以跟徐小平同台演讲,然后放他鸽子……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合伙人
写于2014年圣诞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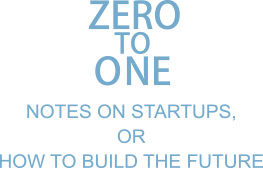
今天,企业短兵相接地展开激烈的竞争。市场仿佛一块有限的饼,当你不能勇猛地切得比别人更大时,你就开始落后,最后甚至出局。于是企业之间开始比拼速度,比拼执行,比拼谁能更快更好地复制和翻版新潮产品或商业模式。纵然如此努力,大多数企业仍然逃不脱靠微薄利润度日乃至亏损被淘汰的命运。
在彼得·蒂尔看来,这就是“从1到n”的宿命。走在这条路上的企业厮杀在红海里,它们奉行的生存法则是从竞争对手那里夺食,出路就是足够勇猛,以在惨烈的竞争中做到第一。彼得·蒂尔认为,这种只会死盯着“有”,而局限于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实在不怎么高明。他推崇的是“从0到1”,或者说“从无到有”,“道生一”的智慧。这通过创新,给人类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创造新价值,让整个蛋糕变得更大。
20世纪中期技术高速发展,仅在1969年就发生了两件大事:人类登上了月球和互联网诞生。于是大家期望这个世界发生很多的“从0到1”,比如能源便宜得压根儿不用计量,能到月球上度假等等。然而这些期望都落空了,在彼得·蒂尔看来,唯一获得大幅度改善的是计算机和通信的发展。他常感叹:我们曾经想要会飞的车,如今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推特等新媒体以140字符为限)。
从0到1,或者说从无到有,意味着企业要善于创造和创新,通过技术专利、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品牌等形成壁垒,从而实现质的垂直性层级跨越,由此开辟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蓝海市场而成为这个市场的唯一,这样的垄断足可让企业安享丰厚的利润。
即便对整个商业社会而言,这样的模式也开辟了非零和游戏的疆域,着眼创造新价值,把市场的饼做大,这才是最终商业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救赎之道。而与之相对,从1到n只是复制,创造不了新价值,甚至可能沦为遍地抄袭的山寨模式。
“从0到1”与“从1到n”的对比
| 从0到1 | 从1到n |
| 创新 | 复制 |
| 质变 | 量变 |
| 垂直 | 水平 |
| 蓝海 | 红海 |
| 垄断 | 竞争 |
| 唯一 | 第一 |
| 非零和 | 零和 |
| 厚利 | 薄利 |
以此为维度去审视当代的企业,我们可以把企业的经营境界分为三层。
第一层境界:企业只是制造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只要有原型,工业流水线可以让产品大量地复制生产出来。但产品有生命周期,市场有饱和度,利润空间也有限,这就是典型的从1到n的过程,只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只是企业追求赢利的过程。
第二层境界: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组织基因,因而可以与时俱进地不断进化,实现纵向的传承,企业最好的产品就是企业自身。比如IBM公司,早期创立时主要业务是商用打字机,昔日和今日的产品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但创建百余年来,IBM建立的文化和制度基因是不断传承的,这推动IBM不断进化,持续创造商业的辉煌。不过这样的纵向传承仍然还是在企业内部,仍然属于从1到n的过程。
第三层境界:企业创造了社会基因或者思想基因,这可以跨越企业的边界,影响到整个行业乃至社会,实现横向的传承。比如苹果,它的成功远远超过了电脑或者手机单纯产品的范畴,影响也绝不仅仅限于苹果公司内部。甚至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深深打上了苹果的烙印,这就是从0到1,企业创造的基因影响了社会文化和观念,乃至改变社会进程,这就是质变。
从0到1的重要性也不见得被所有思想大师所重视。如最近非常热门的《21世纪资本论》,在我看来,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论述非常精彩,但其中却有一个不足,就是他忽略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不是说市场上有玩家的发展速度超过GDP就一定会有其他玩家受损。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的作用而单纯讨论公平问题是有失偏颇的。托马斯·皮凯蒂的理论在从1到n的世界里可以成立,但他忽略了从0到1给人类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和创造的新价值。
这也类似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对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的区分,有限游戏在边界里玩儿,是一种零和游戏,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玩家只是在既定规则下争做赢家,有人赢就一定有人输。但无限游戏玩儿的就是边界,是一种非零和游戏,没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玩家可以不断加入,新价值被不断创造出来,游戏因而可以不断延续。
值得关注的是,这本《从0到1》绝非学术讨论或者思想大师们的论战,它自问世起影响就迅速超越了投资圈,在美国亚马逊图书畅销总榜上跻身前列。我在硅谷和彼得·蒂尔共进早餐聊起这本书时,他也流露出对这本书寄予厚望,期待通过亲身实战经验和心得的分享,真正推动这个世界,当然包括当前山寨泛滥的中国有更多的“从0到1”。
《从0到1》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彼得·蒂尔深入剖析了对于当代企业突围竞争红海至关重要的“大道”,更在于这本书凝结了他身经百战的智慧和经验精华。彼得·蒂尔是赫赫有名的“PayPal黑帮”教父级人物,也是曾在谈判桌两边都坐过的人,(曾做过创业者融资,也做过投资者),他是Facebook的第一个外部投资者,仅这项投资就让他赚得上千倍的回报。
之所以被冠以“黑帮”的名头,是因为PayPal这个深具“从0到1”基因的支付公司,走出了许多商业领袖,衍生了不少名震商界的公司。如领英网的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YouTube的联合创始人陈士骏,继乔布斯之后硅谷新的一位创新领袖,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特斯拉的掌门人埃隆·马斯克等等。我和唐彬从硅谷回国创立易宝支付,也正因为深受“PayPal黑帮”这种从0到1基因的影响。2013年,我参与央视大型纪录片《互联网时代》的制作,也专门造访了埃隆·马斯克、里德·霍夫曼和陈士骏等,他们正是互联网史上“从0到1”的典范。
这本《从0到1》要勾画的是“从0到1”的可复制基因,因此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醒我们“从0到1”的重要性,而更重要的是分享彼得·蒂尔亲身实践过的可操作方式和可行路径,相信《从0到1》在中国的问世,一定能给中国诸多拥有梦想,不甘于山寨模式而期待通过创造新价值去把握明天的创新者、创造者、创业者带来全新的启发和前行的动力。
余晨,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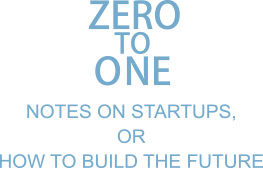
商业世界的每一刻都不会重演。下一个比尔·盖茨不会再开发操作系统,下一个拉里·佩奇或是谢尔盖·布林不会再研发搜索引擎,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也不会去创建社交网络。如果你照搬这些人的做法,你就不是在向他们学习。
当然,照搬他人的模式要比创造新东西容易。做大家都知道如何去做的事,只会使世界发生从1到n的改变,增添许多类似的东西。但是每次我们创造新事物的时候,会使世界发生从0到1的改变。创新的行为是独一无二的,创新发生的瞬间也是独一无二的,结果新奇的事物诞生了。
美国的公司,如果不在艰难的创新上进行投资,不管现在有多挣钱,将来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如果我们对已有业务进行调整,获取了它能给予我们的一切,会怎样呢?尽管听起来不可能,但答案似乎比2008年的危机更糟糕。今天的“最佳方法”可能会把我们引入死胡同,而最佳途径是未经尝试的新路径。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私营还是公共机构,管理体系都极为庞大,寻求新的途径就像是希望奇迹出现一样。事实上,如果美国的工商企业想要成功,需要成千上万个奇迹的出现,这实在是太让人沮丧了,但有一件重要事情除外: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物种,是因为人类有创造奇迹的能力。我们称这些奇迹为科技。
科技是神奇的,因为它能让我们事半功倍,将我们的基础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他动物受本能的驱使可以建造蜂巢等,但是,只有人类能够创造新事物,想出新方法。人类决定建造什么并非基于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基本选项,而是通过创造新科技,重新改写世界历史。这是我们教给小学二年级学生的基本常识,但是,在这个不断重复已有成果的世界中,它却很容易被人遗忘。
《从0到1》一书是关于如何创建创新公司的,主要基于本人作为PayPal和帕兰提尔公司(Palantir)创始人,以及Facebook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上百家初创公司投资者的经验写就。虽然我注意到许多模式,书中也有所涉及,但是本书绝非成功秘籍。创业秘籍并不存在,因为任何创新都是新颖独特的,任何权威都不可能具体规定如何创新。事实上,我注意到一个最为重要的模式:成功人士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价值,他们遵循的是基本原则,而非秘籍。
此书源于2012年我在斯坦福大学所教授的一门关于创业的课程。大学生可能娴于几项专业技能,但是许多人从未学过在广阔的世界中如何应用这些技能。我教授此课程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学生超越学术专业设定的路径,开创广阔的未来。我的一个学生布莱克·马斯特斯记下了详细的笔记,在校内外广为传阅。在《从0到1》一书中,我和他一起对笔记进行了修改,以适合更广泛的读者阅读。相信创新的未来不会只限于斯坦福大学或者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