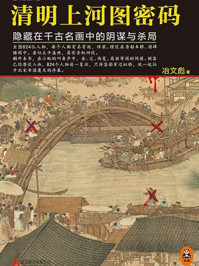五件命案
五件命案

在白老板被杀的同时,朱圣听扶正了头上的瓜皮棉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巡抚大院。
怒气冲天的王幕安,上来就是劈头盖脸一通臭骂,什么玩忽职守、失职懈怠,总之所有能想到的罪名,全都安在了朱圣听的头上。最后下达了任务:半个月内,必须剿灭沙子垅的土匪,荡平山巅寨,夺回被抢的行李和财物,少一件就提头来见!
朱圣听一边赔着笑脸,一边暗暗叫冤,知府大人明知要挨骂,就以病推托,让他这个师爷来顶口水。再说了,沙子垅的白老板每月初一和十五按时给府衙送“份子”,比朝廷的俸禄还准时,这说剿就剿,不是断自己的财路吗?
驰报知府大人,知府大人倒是痛快:“剿!”土匪得罪得起,巡抚大人可得罪不起,虽说是退休的巡抚,可到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等到了规定的最后期限,朱圣听拿着兵符去新军营抽调了五百人,抄上家伙就奔沙子垅而去。途经巡抚大院门外,所有人一起摇旗呐喊。在王幕安的眼皮子底下,场面必须做足,而说到剿匪,倒不会真剿,只是去劝劝白老板,让他归还财物,然后搬家去别的山头而已。
然而令朱圣听没有想到的是,往日半里一门营的沙子垅,今日一连四个关卡竟全都无人把守。抬头仰望,山巅寨静悄悄的,似乎鬼影子都没一个。
山巅寨的夹板门大敞,朱圣听还在几百步外,就嗅到了风中飘来的血腥气,刺激得他胃脏倒腾,直欲作呕。
进入寨子,眼前的景象,令朱圣听和随行的五百名士兵心惊胆寒!
寨中三厅十二院,到处都是死人,上百号匪崽子,竟全部被灭口,或被割首,或被穿胸,或被腰斩,死状极其惨烈,每具尸体的脸上或手上,都发现了血写的数字,其中数字“十一”最多,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地上的血液尚未完全凝固,应该是一两个时辰之前刚发生的。只有关在牢房里的二十来个人还活着,这些人大都非老即弱,是遭匪崽子抢劫后,被抓上山来当苦力使的。据这些人讲述,事发当时,牢房外一片鬼哭神嚎,根本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朱圣听急忙派人搜查寨子,发现所有抢来的财物都在,这才松了口气。
朱圣听虽说是府衙的师爷,吃公家饭的,可骨子里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脾性,奉若圣旨的人生原则就是得过且过。眼前这等死上百人的非同小可之事,如果发生在太平年代,上面有人盯着,或许还要硬着头皮管一管,但眼下时局混乱,朝廷风雨飘摇不说,各地的衙门和军阀更是暗怀鬼胎,甚至可以说随时都有可能改朝换代。上头的官僚们个个忙着拉关系寻靠山留后路,谁会来管这鸟不拉屎的山头?朱圣听定了定神,决定此事就这么着,不往深了调查,反正死的都是一群可有可无的土匪,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不愿也不敢在这凶险之地久留,只求不招惹是非,能向王幕安交差就行。
朱圣听一把火烧了山巅寨,也算是处理了上百具尸体,以免发生瘟疫,顺着水源传播,接着把幸存的二十几个老弱苦力放了,押着财物下山,来到巡抚大院,对王幕安说已经剿灭了土匪。王幕安远远望见沙子垅方向浓烟冲霄,也就信了。王幕安要回了被抢的行李和财物,又格外相中了几件古董。朱圣听私留了几件珍品,又挑了几件上等货转送知府大人,剩下的,一部分分给手下的士兵,一部分上缴朝廷,也算是功劳一件。
只是山巅寨被灭口的景象,在往后的时间里,一直阴魂不散地纠缠在朱圣听的脑海里。
王幕安运气不错,不但追回了财物,还白捡了几件上等古货,算是小赚了一笔。
在这几件古货当中,有一件十分奇特,是一块径长五寸、厚约半寸的圆形木盘。木盘一面光滑,另一面刻有九个很奇怪的图案,每个图案似乎都不完整,给人一种支离破碎之感。
起初王幕安并没有在意,将这件古货扔在一边,过了几天又想起,找出来把玩,这才发现木盘上的九个图案可以推动,最终拼成一副完整的山水图。这时,咔的一声,木盘的上下层分离开来,原来这九个图案是开盘的机关。在木盘的夹层中,一块方形的铁块掉了出来。这铁块约半个手掌大小,只有一粒米那么厚,上面既无图案也无刻痕,打磨得十分光滑。
左看右看,铁块的六个面光滑平整,普通至极,实在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王幕安不禁大觉奇怪,这样一方平平无奇的铁块,为什么会被如此隐蔽地藏在木盘里?
过了几天,县里的铁匠胡启立,给巡抚大院送来新铸的铁器。既然是铁匠,对铁器懂得肯定多,王幕安就把胡启立叫到书房,拿出铁块,让他瞧瞧可有什么古怪。
胡启立拿着铁块一掂量,就说这东西不对劲。
王幕安问哪里不对劲。
胡启立说:“重了。”
按照胡启立多年和铁器打交道的经验,这么大小的一块铁,不会有这么重。
“这铁块里头还有东西,别的东西。”胡启立很肯定地说。他说这话时,额头上的疤痕,跟随岁月的皱纹一起起伏。
王幕安把铁块交给胡启立,要他拿回去切开,看看里面裹着什么东西。胡启立点点头,拿着铁块,一瘸一拐地走了。
第二天,胡启立没来。
第三天,胡启立还是没来。
第四天,王幕安坐不住了,差人去打铁铺。胡启立不在铺子上,听说出去办事了,不过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家中。去的人在打铁铺守到傍晚,终于守到了骑马归来的胡启立,于是把胡启立“请”来了巡抚大院。
胡启立把切开成两半的铁块还给了王幕安。王幕安见铁块的内部有一个小小的扇形凹槽,就问里面的东西在哪里。
胡启立说里面是空的,根本没有东西。
“你当我是黄口小儿吗?”王幕安拍案而起,“少在我面前装蒜,里面如果没东西,应该更轻才是,你那天怎么会说它重了?”
面对王幕安的喝问,胡启立无话可说。
王幕安认定铁块里藏有宝物,保不定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被胡启立私藏了,于是把胡启立截留在府上,威逼他交出来。胡启立一口咬定里面什么也没有,死也不改口。
胡启立和巡抚家的公子爷杠上,一夜未归家,这个消息好比蒲公英的种子,见风就跑,县城里一下子轰动了,如同炸开了锅,连邻县的人都沸腾了,好像胡启立是什么焦点人物似的。胡启立的老婆连夜赶来,哭着喊着要人,也被王幕安吩咐下人轰了回去。
第二天,朱圣听听到风声,心急火燎地赶来,好说歹劝,让王幕安最好把胡启立放了。
王幕安怒了:“我王某是什么人?他姓胡的又是什么东西?一个臭打铁的,难不成有玉皇大帝撑腰,要你来求情?”
朱圣听见王幕安不肯听劝,只好给他讲了辛丑年,也就是三年前,衡州府发生的五件命案。
衡州府的治安虽然不好,但也不算太差,这些年里发生的命案并不多。但辛丑年间的五件命案,却长时间沸沸扬扬,闹得满城风雨。这五件命案发生在二月到腊月之间,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至今仍未告破。但这五件命案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共同处。首先,五个死者都与胡启立有关系,他们都曾得罪或者说是欺压过胡启立,尤其是其中一个叫何二娃子的烂痞子赌徒,是杀死胡启立小儿子的第一嫌疑人,只不过官府没有找到证据,再加上何二娃子在大牢里耍痞子性,死不承认,最终被释放出来;其次,五个死者的身边,都发现了一节沾有鲜血的竹筒。
至于凶手留下这节竹筒的含义,衡州府的男女老少都在猜测。有人说,竹筒多半代表凶手的身份,很可能凶手的名字里就有一个竹字,凶手这是杀人留名;也有人说,凶手是个自命清高之人,以竹自表;还有人说,凶手说不定是住在某处和竹有关的地方……总之各种猜测,林林总总,应有尽有,莫衷一是。
虽然不能确定凶手真正的身份,但毫无疑问,有一个人从始至终贯穿了五件命案——胡启立。
胡启立作为最大的嫌疑犯被抓进了府衙大牢,但无论如何审问,都得不出个所以然,再加上确实寻不到证据,最后只能将胡启立放了。死者的家属,以及四村八店的街坊邻居,纷纷跑来打铁铺,或威逼或哀求或询问,想从胡启立的嘴里问出点真材实料来,但通过多次接触,所有的人最终都判定,胡启立确实对此事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他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有人只能猜想,很可能是有人躲在暗中,为胡启立报仇雪恨,讨回了公道,至于是谁,连胡启立本人也不知晓。从此以后,衡州府所有的人,都变得知趣了,再没有人敢轻易去招惹胡启立一家人。
得知这五件命案后,王幕安也多少被吓到了。虽然是个我行我素的纨绔子弟,但对于危及性命的事,王幕安还是十分惧怕的。一个人越是富有,就越是怕死,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所以王幕安当场就拍胸口表态,不会再去找胡启立的麻烦,并当着朱圣听的面,把关了一晚上的胡启立给放了。朱圣听得到了王幕安的保证,松了口气,放心地走了。
但是王幕安不找胡启立的麻烦,并不代表他不找回铁块里的宝物。
当天晚上,他左思右想,还是不肯吞下这个哑巴亏,就派了四个手下去打铁铺,找胡启立要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千叮咛万嘱咐,要四个手下必须客客气气,不能硬来,即便实在要不回,那也罢了,回来从长计议就是。
去的四个手下,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天亮的时候,消息传来,胡启立一家四口惨遭灭门,打铁铺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王幕安当场就蒙了,急忙派人去找办事的四个手下,哪知却怎么也找不到。
张明泉验过四具焦尸,并受蒙面人的威胁而做了假证,说死的是胡启立一家四口,是被利器先杀死,然后被大火焚尸灭迹。
王幕安心想,派去办事的四个手下,一定和胡启立闹僵了,一时冲动动了手,结果不小心闹出了人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胡启立夫妇和一对子女一并杀死,然后放火烧毁现场,脚底抹油跑路,可是这个黑锅,却最终要扣在王幕安的头上。
果然,王幕安派人杀死胡启立全家的传闻,很快就在坊间传开,成为衡州府人人必备的谈资,走到哪里,被人问起,如果不知此事,那是要遭人笑话的。
朱圣听风风火火地再一次赶来,找王幕安问清楚了情况,回去禀报知府大人,随后派出大批公差,四处查找逃逸的四个手下,但一直杳无结果。
于是王幕安开始了日夜不停地担心,于是衡州府的每个人都挂怀起了这件事。人人都在想,辛丑年间的五件命案,还会不会再一次上演。
到底是众望所归。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虽然迟到了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