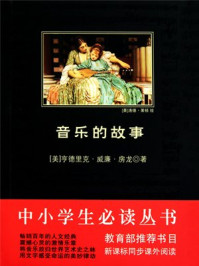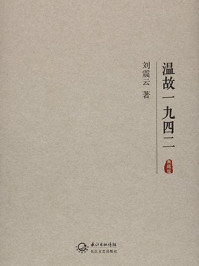传播学是舶来品。国际传播学也是如此。国际传播的学名译自英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指的就是国际间的传播活动。国际传播学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和国际政治学。
国际传播学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20世纪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十二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了三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中,20世纪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 、《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
 。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五家
。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五家
 。
。
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近二十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所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三本,一是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蔡帼芬主编《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以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当然,目前中国国际传播学还存在一些弱点,主要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国际传播最直接的学科来源就是传播学(包括新闻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20世纪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这一发展过程与这一时期人类传播方式的改进相伴随。80年代以后,美国各大学每年提交的传播学博士论文大约为120部,占论文总数的千分之四。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四千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
 另一位日本学者者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
另一位日本学者者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
 由此而来,传播学对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等问题方面,也就是说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由此而来,传播学对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等问题方面,也就是说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国际传播的另一个重要学科来源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世纪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
 。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全球化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全球化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恩格斯说,“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十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十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国际传播学的研究,包括许多丰富的内容,比如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而这些研究都与译制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五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
那么,译制片作为跨越国界的媒介文化信息交流,在国际传播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正是译制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相互联系的重要表现。
再比如,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做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看率、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同样的问题是,译制研究与国际传播的策略研究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国际传播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际传播学为译制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译制研究也应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国际传播的重点主要还在国际关系、民族文化策略、信息流通这些宏观层面,很少细化到具体某类媒介产品(如新闻编译、影视作品译制)的语言转换问题上。这说明译制片的研究为国际传播学的深化提出了不可回避的新课题,而译制研究也将促进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