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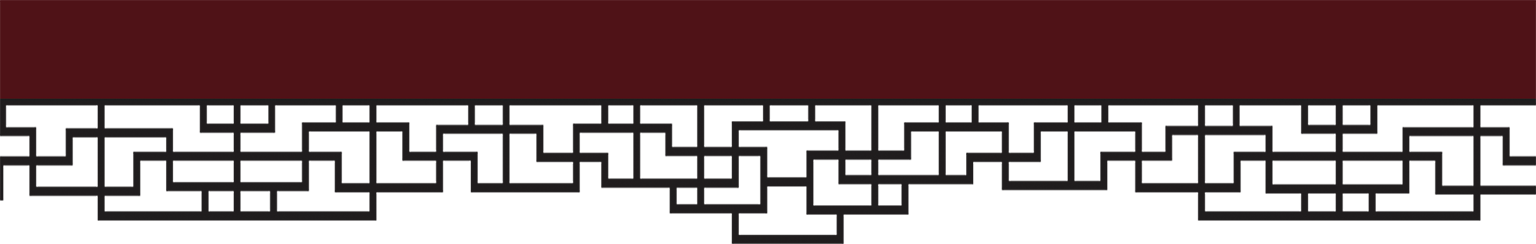
《红楼梦》是了不起的。它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空前未有的东西,就是把女人当人,对女性尊重。
封建社会把人不当人,尤其把女人不当人。中国古典文学尽管写出了不知多少美丽的女性的形象,但是,其中最高的也不过是敢于为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而斗争的可爱的形象,例如崔莺莺和杜丽娘;其次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可同情的形象,例如刘兰芝和杜十娘;再次是可怜悯的形象,例如“宫怨”诗、“思妇”诗的主角;最低的则是供玩弄供侮辱供蹂躏的对象,就是那些宫体诗艳体诗的主角……
这还不一定是最低的。还有“三言二拍”里面那些女性,总是抢劫、欺骗、拐卖的对象;《金瓶梅》里的女性,是以受侮辱受蹂躏为乐为荣的卑贱污浊的形象;《水浒传》里的孙二娘、顾大嫂,是“母夜叉”“母大虫”的形象;扈三娘是无意志,无感情,全家被梁山好汉杀了,却听凭宋江指配给曾是她手下败将的王矮虎,从此自自然然地入了梁山一伙,好像是个机器人似的形象;潘金莲和潘巧云,则是活该在英雄好汉的刀下剖腹开膛的“淫妇”形象。
这样一比,就看得出《红楼梦》确实伟大。作者曹雪芹自己说得很清楚,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使闺阁昭传”,就是要使天下后世知道“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灭也”。封建眼光把女人看作“贱人”,第二等的人。曹雪芹却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他为了这个目的来写,也的确写得很成功。在他笔下,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晴雯、鸳鸯、紫鹃、平儿……几十个青年女性,不仅仅是美丽,不仅仅是聪明,而且首先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行止见识”不凡的、有独立人格的人。在她们之中,还有一个男孩子贾宝玉。贾宝玉不仅爱她们,尊重她们,还尊重世界上一切青年女性,他真心坚信“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真心坚信“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这个贾宝玉,其实倒是女娲补天石锻炼而成的“通灵宝玉”的化身,真正是“山川日月之精秀”。
冯雪峰说过:从封建压迫下觉醒的女性,“往往要通过女性的觉醒,去体验着她们之‘人’的社会的觉醒”,这说的是“五四”时期的梦珂、莎菲式的女性。中国古典文学里面,初步有点“女性的觉醒”的味道的,大概要推《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些唱词之所以那么感动了当时女读者们,就因为它唱出了初步的“女性的觉醒”。徐朔方说得好:杜丽娘“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春天,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生命是和春天一样美丽”。《红楼梦》也写了林黛玉听到这些唱词,而“感慨缠绵”、“心动神摇”、“如醉如痴”的心境,这是黛玉的被唤起的“女性的觉醒”。《红楼梦》并不到此为止,它还让一个优秀的男性对女性唱出那么热烈的颂歌,这就比《牡丹亭》又大大前进一步。
中国封建社会对女人特别残酷。我们今天当然都知道,压迫妇女的,根本上是制度,不是男性。但在那样的制度下,恐怕没有一个男性不是夫权主义者、大男子主义者,没有一个男性不是自以为高出妇女一等,把妇女视为花鸟、玩物和工具,骂她们是“贱人”。妇女解放的斗争对象当然不是男子,但妇女解放的每一步,无可避免地要同男子这种贱视妇女的态度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几千年的黑沉沉的囚禁和虐杀女性的牢狱中,竟然第一次听到“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样的呼声,这是多么了不起!这样的呼声,如果出自女儿之口,例如黛玉就说过:“什么臭男人!”当然也使人不能不另眼相看。但现在是出自男子之口,他不但不以“男子汉大丈夫”在女性面前自骄,并且不以“通灵宝玉”的化身自骄,而是由衷地自惭形秽,自称“浊玉”,想想看,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又何尝不可!
这也许有些矫枉过正。男性和女性都把自己和对方看作平等的人,才是正常的、自然的态度。但文学本来有异于科学。文学家要写的是活生生的人,是活的感受和感发,它们是否合乎科学,不是一眼看得出来的,有时看似偏颇,恰好包含着合乎科学的内容。鲁迅的《伤逝》里面,由一般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经过实生活里男女人生境界、胸襟智能的不平等的暴露,导致悲剧以后,归到男性的道义上社会责任上的深沉痛烈的自责。这也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的层次上,继承了《红楼梦》中男性的自惭。《伤逝》以后,还没有听到过嗣响。而涓生的绝叫中包含的真理内容,至今也还没有探讨完。
《红楼梦》既是女性的颂歌,又是女性的悲剧。
故事的中心地位,是贾宝玉和他的表妹林黛玉、表姐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宝玉在黛玉、宝钗之间究竟爱谁,贾府究竟选谁作宝玉的妻子,这是一个大问题。悲剧产生于两个选择的不一致。宝玉越来越发现黛玉是唯一的知己,宝钗虽也可爱可敬,心灵上总有一层隔膜。贾府的当权者们即宝玉的祖母和父母,则是越来越发现宝钗符合贤慧儿媳的标准,黛玉的性格气质却隐隐含有某种叛逆性;宝钗能把对宝玉的爱尽量克制在礼法的范围之内,黛玉却往往作了执着的表露。悲剧尤其产生于两个选择的权威性大相悬殊:爱不爱谁,宝玉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但是,娶谁作妻子,宝玉自己是一点权利也没有的,一切决定于父母之命。于是,悲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环绕他们三人的还有一大群少女少妇,青春守寡的是史湘云、李纨,出嫁一年便被丈夫折磨死了的是贾迎春,远嫁的是贾探春,悲观绝望青春出家的是贾惜春,跳井而死的是金钏儿,含冤而死的是秦可卿和鸳鸯,撞壁而死的是司棋,斥逐羞忿而死的是晴雯,被强盗抢去的是妙玉……她们都是“薄命司”册子上注定没有好结局的人物。
这里面,有封建婚姻制度的悲剧,有封建道德礼教的悲剧,有封建婢妾制度的悲剧,有赤裸裸的封建暴力凌辱女性的悲剧,……她们在那个社会里,处于显贵的上层,即使是丫环,平常饮食起居也是平民家庭望尘莫及。她们尚且如此,下层女子的命运可想而知。总之可见,这不是某一个女性某一个问题上的悲剧,而是那个社会里青年女性的普遍悲剧。曹雪芹用她们的泪水酿成了芳醇甘冽的艺术之酒,这就叫作“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又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可见,无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不是悲剧,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才是悲剧,价值愈高,悲剧愈大。女人如果只是花鸟,只是玩物,她们的毁灭顶多能博得几声叹息,一番惆怅;如果是“小贱人”,什么命运都是活该。中国历史上,围城之中,什么都吃光了,主帅便带头杀了爱妾,分给军士吃,然后把城里的女人全捉来吃,然后才吃到老弱的男性,这样的事例史书上多得很,而且不是野史,都是煌煌的正史。那些杀爱妾以饷士卒的将军们,当然是同杀一条爱犬差不多。到了大规摸吃女人的时候,更没有人会想到,被吃的她们也是人,有美丽聪明的,有才华横溢的,有情韵雅洁的,有志行高卓的,……统统象吃猪肉羊肉一样地吃掉了。
《红楼梦》的悲剧之所以特别震撼人心,就因为它充分写出了被毁灭的女性不仅外形是美的,而且内心更是美的。
就拿林黛玉来说,书中充分写出了她的品格,她的思想感情,她的幻想和追求,她的高出流俗的“行止见识”……读者如果不是了解了这一切,深深感到这是一个高洁美好的人,如果不是久已感她之所感,爱她之所爱,和她同忧同乐,同笑同啼,她的悲剧就不会使读者这样回肠荡气,惊心动魄。
书中多次写了女孩子们结社吟诗,或是自吟自咏,这是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段,让她们直接抒发心情。于是,读者听到了黛玉的悲吟,知道“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大观园,在她眼里却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场所,知道清幽的潇湘馆里,她过的是“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直到“不知风雨几时休,己教泪洒纱窗湿”的凄凉长夜。读者还听到她对着菊花低吟道:“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似乎窥见她所期望于宝玉的,不仅是“男才女貌”相当的“如意郎君”,而且是在茫茫尘俗之中可以“偕隐”的“知心”者。如果读者不知道这一切,就不能充分体会她含恨而死时最后那句没有说完的话“宝玉,宝玉,你好……”的全部惨痛的含意。
笼照全书的《红楼梦曲子》,更是直接的女性颂歌的大联唱。它歌颂黛玉是“世外仙姝寂寞林”,歌颂宝钗是“山中高士晶莹雪”,尤其是歌颂湘云道:“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歌颂妙玉道:“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羶,视绮罗俗艳,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更是高度的尊敬,满腔的同情!读者听了这样的颂歌,才能深刻感受她们的悲剧。
《红楼梦》作为对女性的颂歌,不仅加强了它作为女性悲剧的力量,而且是它之所以能够写出女性悲剧的原因。这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青年女性的悲剧,早已演出了一两千年。直到曹雪芹,才把这个悲剧写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把女人当人,尊重女性,才看得出这是悲剧。“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有曹雪芹,才看得出青年女性是“山川日月之精英”,才看得出写得出她们的悲剧的命运。有才情的女子常有,而曹雪芹也是不常有的。
前面说过传统的“宫怨”诗,已经算是同情那些不得宠的妃嫔宫女了。但是,替她们“怨”什么呢?“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入时十六今六十。”见了又怎么样呢?原来怨的只是没有得到“君王恩幸”罢了,直白地说,只是没有受到封建帝王的玩弄罢了。如果用这个眼光看,宝玉的大姐贾元春,入宫受宠,晋封贵妃,全家沾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该是多么幸福!总该不是悲剧了吧!可是,曹雪芹也把她列入“薄命司”的册子,写她奉旨回娘家省亲,说不尽的繁华热闹、富丽庄严之中,从头到尾却是一片呜咽哽噎之声,在艺术上达到“以乐景写哀”的极致。对元春的描写只是寥寥几笔,但是她公然埋怨父母当初送她入宫是把她送到牢狱一般的“那见不得人的去处”,只这一笔就使读者隐约窥见她的内心深处闪烁着某种高出流俗的光辉。
曹雪芹的眼中才看得出的悲剧,在《红楼梦》的艺术世界里,就是贾宝玉的眼中才看得出的悲剧。
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从宝玉的角度来看,而是从贾母、贾赦、邢夫人、贾政、王夫人的角度来看,所有女孩子的悲剧,都不成其为悲剧,有的是咎由自取,有的是死有余辜,有的是命中注定,有的是偶然事件,……例如,贾母认为黛玉的死,是死于她自己的“心病”。王夫人认为晴雯的死,是死于她自己的“女儿痨”。贾赦认为迎春的死,是死于她自己的“命”;鸳鸯的死,是公然要逃脱我老爷的掌心,正是活该。至于贾珍、贾琏、薛蟠之流淫魔色鬼的心里,怎样想那些美丽的女孩子,更是不可问。
便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如贾政者,心里又何尝干净呢?他听说儿子宝玉从小就宣布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那些话,便十分不喜,认为这个儿子将来不过是“淫魔色鬼”、“酒色之徒”。可见这位正人君子眼里,女人仅仅是性的对象而已,男人除了“淫魔色鬼”“酒色之徒”而外,都不会也不应该对她们发生兴趣,也可见被贾政认为“淫魔色鬼”的宝玉眼中所见的悲剧,从贾政看来都不是悲剧。
宝玉其实并不是“淫魔色鬼”,而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母腹中开始孕育的“新人”的胎儿。除了自家姐妹而外,他对周围那些美丽的青年女性是爱的,他的爱要说全无直接间接或隐或显的性爱成分,也不符合书中写明的事实。但是,他的爱却有一个全新的性质,这就是鲁迅深刻地指出了的:“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
“昵而敬之。”说得真好!昵,就是多少含有性爱因素的爱。何其芳曾经指出,贾宝玉这个典型形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多情”。这是说得对的。但是,宝玉这种“多情”,不但不是西门庆式的兽性的占有,甚至也不是晏小山、纳兰容若那种“多情”所能比拟。新就新在加上了一个“敬”字,这就大大不同了,惟其“昵而敬之”,方能看出所敬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悲剧,把她们每一个人的悲欢哀乐,荣辱得失,都包括在自己的关心注念当中,这就叫作“爱博而心劳”。
这就是说,宝玉感受到的,不只是他自己的悲剧的重量,加上所有青年女性的悲剧重量的总和,而是远远超过这个总和。因为身在悲剧中的青年女性,特别在那个时代,远不是都能充分感受到自己这一份悲剧的重量,更不能充分地同感到其他女性的悲剧的重量。例如平儿,宝玉深深同情她夹在“贾琏之俗,凤姐之威”当中的不幸处境,替她愤恨贾琏之“惟知以淫乐悦己,不知作养脂粉”;可是她自己却一味“周全妥帖”,不仅看不出有什么不满,就是平白无故挨了凤姐的打,稍经调停反倒跪下来给凤姐磕头谢罪:“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气,是我该死。”事后照旧贴心得力地当凤姐的助手。又如香菱,从小被拐出来,卖到花花太岁式的恶少薛蟠手里,已经够不幸的了,可是她一味憨头憨脑地学作诗,似乎一点不幸之感都没有。
甚至林黛玉,她对自己的价值,对自己的悲剧,也未必能象贾宝玉认识的那么深刻。宝玉最敬她的,是她从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路。但是,宝玉是常常不得不参加“峨冠博带”的场合,见惯了那些讲“仕途经济”的人,厌恶他们。黛玉则是一个深闺少女,不可能有同样的阅历,对于“仕途经济”不可能达到与宝玉同样的认识水平。而这一点认识水平上的差距,就使黛玉不可能充分估计自己在宝玉心中的价值,和自己的悲剧在宝玉心中的分量。宝玉在黛玉面前说“你死了,我当和尚”,黛玉很不愿听,几次为此生气,恐怕她只把这句话理解为一般的爱情的誓言,不理解自己在宝玉心目中是人世最高价值的体现,不理解自己如果死了,对宝玉不仅是爱情的毁灭,而且是人世最高价值的毁灭,这样的人世当然不值得留恋。
宝玉就是这样的“爱博而心劳”。比所爱者本人还要操心,还要忧深虑远,自然是“而忧患亦日甚矣”。几千年来被否认的女性的价值,仅仅在宝玉眼中充分反映出来,几千年来被遮掩住的女性的悲剧,也仅仅在宝玉眼前拉开帷幕,所以鲁迅又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红楼梦》虽是女性的悲剧,女性的颂歌,全书最中心的人物,还是男性的贾宝玉。前面说他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母腹中开始孕育的“新人”的胚胎,他为女性唱颂歌,唱悲歌,都是他作为“新人”的表现。
所谓“新人”,就是有了“人的觉醒”的人。但是,贾宝玉的觉醒,不是看到了自己是个“人”,自感人的尊严,倒是看到自己是人当中的“渣滓浊沫”,自惭形秽。这似乎很奇怪,其实也不奇怪,无非是因为他还仅仅是“新人”的胚胎的缘故。
贾宝玉对女性的尊重,并不是来自理性的认识,而是来自直接的感受。他对一切“峨冠博带”的“须眉男子”深恶痛绝,又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身边,长期接触到那么多的聪明美丽的青年女性,看到她们受到不应有的轻视,看到她们的地位是那样屈辱,命运是那样悲惨,对她们又爱又敬,为她们又悲又愤,回过来就更对“须眉男子”深恶痛绝。他对女性的尊重,看来也许有过于美化的地方,其实那只是他所理想的最完美的“人”,穿着女装的形象罢了。他在穿着女装的“人”面前自惭形秽,就是以理想的完美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实际上,人类的“渣滓浊沫”并不是宝玉,而是贾琏、贾环、薛蟠之流,正因此,他们决不会自惭形秽,他们正自幸生为“须眉男子”,可以玩弄女人,奴役女人,在女人面前自觉高她们一等。
贾宝玉对女性的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人”的尊重。他理想着完善的“人”,但是现实中的男人他觉得太丑恶了,只有美丽的女性才比较能做他塑造“人”的完美形象的原型。他唱的女性的颂歌,其实就是“人”的颂歌。但是,他又眼见一幕又一幕的女性的悲剧,眼见这人世间仅有的美,逃不了毁灭的命运。他念着《芙蓉女儿诔》,其实就是悼念整个的“人”的毁灭;他痛哭潇湘馆,就是为“人”的毁灭放声一哭。
今天我们来看,当时“人的觉醒”才开始,怎么就见到了“人”的毁灭了呢?贾宝玉未免太悲观了吧!其实这也是难怪的。甚至历史已经发展到“五四”运动以后,大革命以前,据鲁迅分析,尚且是这样的:“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这就是说,热烈,是由于爱人;悲凉,是由于觉醒;开始觉醒者寻到的光明总是微弱的,只照到身边一小圈,更反衬出圈外的黑暗的无涯际。在两百年前的青年贾宝玉,他心中那点光明更加微弱,照亮的圈子更小,反衬出周围的黑暗更无涯际,他的心情更加热烈而悲凉,当然就是不足怪的了。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贾宝玉所能寻到的一点光明虽是微弱的,他的心情虽是悲凉的,他这个艺术形象作为“新人”(尽管还只是胚胎)的力量却是强的。这个艺术形象十分可爱。书中有人给他钩出一幅速写肖像:他自己被烫了手,倒问烫了他的那位姑娘疼不疼。他自己大雨淋的水鸡儿似的,反提醒一位姑娘赶快避雨。没人在跟前,他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看见鱼儿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他甘心为丫头充役,受丫头的气。他爱惜起东西来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糟蹋起来值千值万都不管了。他聪明而憨厚,女性化而不侧媚。他喜欢女孩子们,也为女孩子们所喜欢,尤其林黛玉是他唯一的知己。可是,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认为他“乖僻邪谬,不近人情”,认为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轻一点说也是有“痴病”,……这样看宝玉的,不是他的仇人,而是疼爱他的祖母、母亲,和“恨铁不成钢”的父亲,他们的观念都是当时最正统的观念。贾宝玉这样复杂的形象,带着光辉和芳泽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一件小事。
在《红楼梦》以前,中国文学作品里有许多忠良被谗,英雄失路,才人不遇,公子落难,佳人薄命,等等。他们不管遭遇到什么不幸,同当时的环境是协调的,同当时的政治道德观念、真善美的标准是协调的,就是说,他们代表着当时舆论公认的正义和美好的力量,在作品里总是能得到当时正直、善良的人们的了解、赞助和支持。而迫害他们的人,不管怎样嚣张,总归为当时的清议所不容,公认为奸邪,为丑类。即使是梁山好汉,他们的“忠”也好,“义”也好,“替天行道”也好,仍然包括在封建伦理观念的体系之内。《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是中国文学作品里第一个正面人物而不大被了解的,但不了解他的只是那些鄙俗的八股之士;此外毕竟还有虞博士等人了解他,而虞博士等人仍是理想化了的封建人物。
只有贾宝玉,才是同他的环境完全不相协调的。他的整个的性格,同当时社会,同他所属的阶层,完全格格不入。他只好逃到女儿国里去,尽管她们——包括林黛玉也未必能从理智上彻底理解他,但却能够爱他,暂时给他一个温暖的存身之所,这种情况又使他在世人心目中更见荒唐乖谬。所以他一出场,作者便用一阕《西江月》描写他与环境的格格不入,其中说他“似傻如狂”,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从而思考一个问题:贾宝玉可不可以算是那位“狂人”的遥遥先驱?
“狂人”并不狂,他其实是从封建中国的母腹中脱胎而出的第一个“新人”,只因为他全面地叛逆了旧世界,便被旧世界视为“狂人”。这是和贾宝玉一样的。这说明他是属于贾宝玉的血统。但是,“狂人”看得出一部中国史都是在仁义道德的掩盖之下的“吃人的历史”,看得出他周围的人,他家里的人,以及他自己,都是“吃人的人”,闻到他们的血腥;宝玉却只看得出所有的男人,以及他自己,都是“泥做的骨肉”,只闻到他们的浊臭。“狂人”看得到“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高呼“救救孩子”;宝玉却只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女孩子们的泪海里。这是二者的差异。这说明相距二百年,“狂人”贾宝玉比他的后代“狂人”,软弱得多,模糊得多,欠成熟得多了。
尽管如此,贾宝玉这个前代“狂人”的艺术形象,带着光辉和芳泽出现,仍然提出了一个极尖锐的问题:究竟是他错了?还是社会错了?曹雪芹,《红楼梦》,《红楼梦》的千千万万读者,一致用美学的评价作出了回答:这样美好的心灵,美好的性格,决不可能是真正的痴狂。那么,与他不相调和,把他看作痴狂的整个社会,显然不可能是合理的。《红楼梦》不仅写了一群青年女性的毁灭,也写到整个贾府的败落,过去很多人说这就是整个封建社会败落的象征,其实未必如此,倒是贾宝玉这样“新人”的出现,从精神上,从审美标准上,宣布了整个社会的不合理,这才真是封建社会将要彻底崩溃的朕兆。尽管书里面还是社会毁灭了宝玉,但这样的社会,在读者眼中,更显出丑恶,更不是合理的存在了。
封建社会果然彻底崩溃了。但是,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是很强的,要彻底肃清,还是不容易的。今天来读《红楼梦》,还觉得有很大的现实性,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况且,文学艺术中一切不朽的典型,一方面有他的一定的时代使命,另方面还有他的不朽的价值。贾宝玉、林黛玉他们,不朽的是性格心灵之美。他们作为典型,每个人都是“这一个”,是不能代替的。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心灵之美,也是不能代替的。人应该无限地丰富自己,吸收一切美好的东西。对于贾宝玉、林黛玉等人,只要你喜欢他们,象一个知己朋友一样同他们相处,爱他们,体贴他们,笑声交响在一起,泪水汇流在一起,你就会受到潜移默化,他们身上那种对于“人”的完美和高尚的尊重和追求,就会感染你,被你吸收。他们的性格心灵之美,最主要的就是要求人生什么都美,要求千姿百态的美,要求无限丰富无限深刻的美,不能容忍任何一点对于美的粗暴和亵渎。谁要是能够多少吸收到这种向往和珍惜,谁的心灵里就多少具有了趋向于无限完美无限崇高的动力。
《红楼梦》写了一大群美人。她们住在大观园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女儿国。贾宝玉是这个女儿国里唯一的男性公民。这个小小的女儿国,在短暂的几年中,充满了“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之美,充满了青春的笑和泪,爱和怨,酒和诗,享受到(今天看来)很有限,而又(在当时一般现实条件下)很难得的极其例外的自由。她们和以前的文学作品里的美人比较起来,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不但容貌美,而且内心也美。第二,美得有个性,至少是二十个左右的主要人物写得个性鲜明,互相之间毫不雷同。第三,她们是现实生活中平常女子,不是仙女,也不是超凡出众的女英雄女才子。第四,她们以平常现实的女儿之身,又体现了非凡的审美理想。第五,她们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姑娘,她们的一切都有一种青春的纯洁的气息,即使是比较有心计有世故的(例如薛宝钗、贾探春),仍然是青春的纯洁的范围之内的心计和世故。第六,她们的爱情纠葛,有灵的成分,也有肉的成分,而以灵的成分为主,主角林黛玉则是纯然“灵”的。
这个芳香美丽的小小女儿国,实际上是贾府的一部分。而整个贾府,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外表之下充满了污浊丑恶的贵族家庭,只有门前一对石狮子是干净的,并且和整个社会的污浊丑恶联成一片。大片的污浊丑恶之中,有一小块芳香美丽。前者暂时容许后者存在,给予后者极有限的(时间、空间和程度上都极有限的)一点点独立。后者在它暂时存在的范围内,以其强大的美的力量,压倒了前者。但前者的顽固的现实力量,始终统治着支配着决定着后者,其影响深入后者,不久便轻而易举地毁灭了后者。
写出了这样丰富深刻的美,写出了美与丑之间这样复杂的相生相剋的矛盾,这就是《红楼梦》艺术上的伟大成就。它一出世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读者一接触它,便感受到那种芳香美丽,那种青春的纯洁的气息,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空前绝后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三国演义》写的是雄主名王、谋臣勇将之事,攻城略地、纵横捭阖之心。《水浒传》写的是草莽英雄、江湖豪杰之事,仗义行侠、报仇雪恨之心。《金瓶梅》写的是恶霸帮闲、淫娃荡妇之事,谋财渔色、献媚争宠之心。这些都是大家久已熟悉的以成年男女——特别是成年男子为主的世界,作者以阅尽沧桑的老眼,看透这个世界的深层底蕴,写出来给我们看,其中有各种各样的美,但没有青春纯洁的美。《西游记》是古之儿童唯一能当作童话来读的作品,其实不是童话,鲁迅把它列入“神魔小说”一类是对的,儿童读起来已经有一些不理解不喜欢的东西,成年以后还爱读的,恐怕不会有很多了。
只有《红楼梦》写的是一个以少男少女——特别是少女为主的世界,然而并不是幼稚无知的世界,作者也是以阅尽沧桑的炯炯双眸,看透了这个世界的深处。大家都知道,他实际上是从自己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中取材的。回忆的温馨,身世的悲凉,更给作品增加了艺术的魅力。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一首云:
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
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
大致可以借用来描述《红楼梦》的写作:书中的取材,大量来自自己少年时代的哀和乐,歌和泣。然而写作的时候,已是经历了几十年的世路周旋,心中夹杂着童心未泯的“痴”和洞明世情的“黠”了。书中的事不等于少年时代的真事,前者已经把后者化为凄丽温柔的一梦。书中的贾宝玉也不等于真正少年时代的曹雪芹,前者只是后者的“童心来复梦中身”。是的,《红楼梦》的独特的卓越的艺术贡献就在这里。少男少女的读者们倒未必真能理解它,反而越是成年,甚至老年,越是爱读,越是能够领略其中深意,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得“童心来复梦中身”的难得的人生体验和艺术享受。
《红楼梦》最初出现,大约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昂贵的价钱,被爱读者争相购阅。那时书名还不叫作《红楼梦》,而是叫作《石头记》;故事没有完,只有八十回,而不是现在这样的一百二十回。但是读者不管,还是争相购阅。明明一部未完成的作品,立刻受到热烈欢迎,世界文学史上不知怎么样,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抄本流传了三四十年之后,1791年才有活字排印本出现,书名改题为《红楼梦》,回数也从八十回增加到一百二十回,故事才完整了。排印本的出版者和编辑者是程伟元和高鹗,据他们声明,后四十回也是原作者曹雪芹写的,不知何故与前八十回分开了,没有流传,现在由程伟元他们费力搜购得来,才使《红楼梦》成为完璧。读者当然更加欢迎这个完整的本子,从此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一直流传下来,八十回本《石头记》逐渐绝迹。
直到民国初年,有几种《石头记》古抄本被学者胡适发现。经过胡适、俞平伯的研究,看出《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特别是与《石头记》八十回的原貌,情节上有许多不衔接,思想上有许多不一贯,艺术上也颇有高低;还核对出《红楼梦》前八十回并非《石头记》八十回的原貌,而是颇有改动,再加上别的证据,于是1921年胡适宣布他的研究结论:后四十回其实是高鹗写的,他伪称曹雪芹的原稿,今天我们不能承认,其实是曹雪芹写了前八十回,高鹗续写了后四十回。学术界都承认这是重大的发现。从此,关于后四十回的作者究竟是谁,对后四十回究竟怎样评价,成为《红楼梦》研究当中热烈争论的问题之一,意见纷纭,至今未能趋于一致,看来还要争论下去。但是,读者不管这些,要读的还是故事完整的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而不是八十回的《石头记》,尽管他们之中也很有些人认为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差得太远的。反正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存在”,没有人能再把它切开了。
晚近《红楼梦》版本学上又有一重大发现,即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公开面世。此本于道光十二年(1832)传入俄国,沧桑历尽,始赋归来,实乃书林盛事,文坛佳话。这个抄本的底本属于脂砚斋评本,这是毫无疑问的。有的专家研究后认为,它是小说早期印刷前校阅过的最完整的一个本子。例如,抄本第六十七回“馈土物颦卿念故里”一节中,宝玉为了使病中的黛玉高兴,急于把南方带来的土物送给黛玉,描写的文字比其他各本都要长得多。过去印行的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因为没有见到这个极有价值的旧抄本,无法据以校勘,当然也就不可能吸收它的优点。这次李全华同志重新标点分段,特别根据影印列宁格勒藏抄本,在许多地方改正、补入了有关的文字;同时还依照影印乾隆抄一百二十回本,订正了通行本中个别疑误、难解的字;这一点也是值得提出来向广大读者介绍的。
舒 芜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碧空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