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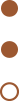
对我来说,在中国有两个地方给我家的感觉。一个是三岔,北京北边的一个村庄,我从2001年起一直在那里有套房子住。另一个是涪陵,长江边的小城,我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生活于此。有时候,我称涪陵是我在中国的“老家”——我想,这其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时候我是认真的。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去涪陵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大多是为美国报纸写的旅行随笔,但从未发表过长篇的,更没写过书。我也从未当过新闻记者。当时,我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并不清楚我要写小说还是非虚构类题材。事实上,刚到涪陵时我仍然认为自己更有可能写小说。在那里的头几个月,我写了一个短篇,故事设定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州。我觉得那是我二十几岁时写得比较好的作品之一,但我发觉还是有点差强人意。文章写完后,我就想:既然我此刻正生活在长江边这个叫人啧啧称奇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去写有关密苏里的虚构故事?于是,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未来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就在中国。
当时,我计划在涪陵尽量多学一点东西,等在“和平队”的服务期结束之后,我想到美国某家报纸或者杂志找一份驻中国记者的活。我并没有想过要写书。我觉得自己太年轻,对中国又知之甚少——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么点时间就想勉强用文字来描述实在显得有点自大和冒失。不过,我在涪陵生活和教书期间,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这段经历相当充实,也相当具有挑战性。我常感觉应接不暇、不知所措,而写日记则大有裨益。到了晚上,我常常会一坐下来就写上好几个小时,力图把我身边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我从学生的作业里摘抄出一个个片段,把城里发生的种种事件记录下来。我还记下了学习汉语的整个经历。总共算起来,我做了好几百页的笔记——我无事可干,写这么多东西倒也轻松。那个时候,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上不了互联网,因此我跟美国那边也没有多少联系。我当时的薪水是每个月一千多块,所以也很少到各地旅游。那期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一处都没有去过。我也打不起越洋电话——当时贵得不得了啊。两年时间,我跟父母通电话可能不到十次。除了亚当·梅耶,我也很少看到外国人。那段时间,涪陵就是我全部生活的重心。
当然,那座城市一直都在变化——在那些日子里,全中国上下都在快速发展着。我在涪陵生活十八个月之后,终于有互联网可以使用了。这一下子就让我跟美国的朋友们恢复了联系,其中就有我大学时的写作老师约翰·麦克菲。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想当一名驻华记者,他随即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在信里面,他这样写道:
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我觉得你应该定下心来写一本书,刻不容缓,要么从这个暑假开始,要么等你的两年服务期一结束就开始,就写你自己的故事……只需以书信形式写上六七万字,就会是一本有意思的书。
那是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考虑写一本有关涪陵的书。我差不多同时也想到了它的题目——我觉得应该就叫做“江城”——接着便开始思考这本书可能采用的写作结构。我规划好各个章节后,觉得应该利用我在涪陵剩下的六个月时间尽可能多地做一些研究考察。我在春节期间有一次长假,我原本计划好要出去旅游的,但后来还是选择待在涪陵,为的就是调研和做笔记。假期过后,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考虑写书的事情。在涪陵的最后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时光之一,我将随时铭记于心。在城里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经过开头艰难的适应期之后,我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汉语,可以跟人们进行交流了;我也交上了知心朋友。我十分乐意跟我的学生、汉语辅导老师,以及姓黄的一大家人一起打发时间。黄家开了一家小面馆,我总是去他们的店里吃饭。我大体上是这样打算的:就写这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刻。我渐渐相信,这个时刻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也坚信,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其实意味着更多。那个时候,外国人一般对中国的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老以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兜里没钱。不过,我认识的所有人——我的学生们、我的同事们、经营餐馆的朋友们,以及我的一个汉语辅导教师——几乎都有那种农村背景。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我因此觉得,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是一个错误。
我在涪陵期间做了详细的笔记,规划了书的结构,但在离开中国之前并没有动笔。我回到了密苏里我父母的家,我已经多年没在那里生活过,如今却坐在了我读高中时曾经用过的那张桌子边上。那个房间的装饰跟我小时候也一模一样。感觉有些怪怪的——我已年满二十九岁,怀揣两张大学文凭,但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实际上,除了在“和平队”当过老师,我一直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我的钱也不多。在美国,一个人二十多岁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还没有工作,会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很庆幸,我一直跟家人十分亲密,并且对自己的写作计划信心十足——尽管如此,我对于何去何从还是有些担心。好不容易抛开这些顾虑之后,我才得以坐下来开始写作。
不过,一旦开始动笔写起涪陵,哪怕刚刚才写第一页,我就已经明白,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文字汩汩涌出,一切都在我脑中活灵活现地冒了出来;当我回过头重读那些段落章节时,它们宛如珠玑一般叮当作响。我意识到,我的写作意欲已经完全改变,调子变得更深沉了;增添了一种新的信心,其中的描述和幽默信手拈来、十分自然。部分原因是我收集写作素材时的认真,但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成熟。我方才明白,在涪陵所面对的那些挑战迫使我成长,而这种新的成熟让我的写作有了新的深度。
就这样,我的写作速度快了起来,每天都能够写上五六页。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没干过别的。我一般上午写作,中午的时候出去跑上十英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下午和晚上我会继续写作。夜里,我会梦到涪陵,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那里了。
我在四个月内写出了《江城》的初稿。期间,我也向美国的各大报纸和杂志寄去求职信。我依旧怀揣这样的梦想——先从给美国的出版物干活儿开始,不论迟早,他们总会派我担任驻华记者。但很快我就明白,没人对我感兴趣。实际上,他们甚至都没有给我亲笔回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费城问讯者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给我寄来的都是格式化的回绝函。只有《洛杉矶时报》给我寄来了亲笔回信。那位编辑说,他很喜欢我写的东西,对我的中国经历也很感兴趣;可我缺乏正式的从业经验,他们不可能聘用这样的人。他还建议我先从美国的小报干起。如果我以此为起点,通过几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最终有望在大报找到活儿干。然后,我得通过苦干来再次证明自己,也许在几年后将担任驻华记者。那样的话,至少需要六年我才能回到中国。
《江城》快要封笔的时候,我收到了最后一封回绝函。这时,我感到身心俱疲,因为我写得太快了。写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理会那些回绝函,强迫自己聚焦于“涪陵”。写完最后一个字,一切都犹如崩溃了似的。我陷入了可怕的沮丧之中——我霎时明白,我二十九了,找不到未来,找不到回中国当记者的路子。至于《江城》,我也觉得糟糕透顶。这本书似乎一文不值——不过小孩子的写作水平而已。我完全无所适从,也想不起我在书里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作家在完成了高强度的写作之后,都有过类似的崩溃体验,就好似十月怀胎的妈妈们一朝分娩,接着遭受产后抑郁的折磨。
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抑郁不已,寝食难安。书稿依旧摆在那里——我无力把它们邮寄出去。还好,我终于恢复了,把书稿寄给了各大经纪人。几乎所有人都回绝了。只有年轻的经纪人威廉·克拉克告诉我,他很喜欢。他把书稿发给各大出版社之后,有些出版社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但他们心怀疑虑,担心美国读者对中国不感兴趣。其中一家出版社说:“书是好书,可我们认为没有美国人想读有关中国的书。”现在看来,这令人难以置信,但1999年早期的图书市场就是这样——美国人还未意识到,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变得多么令人目眩神迷。
不过,威廉还是找到了三家愿意出价购买书稿的出版商,我选择跟哈珀柯林斯签订了出版合同。稿酬不多,但足以让我偿清读大学时的助学贷款。这也令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新的信心。我顿时意识到,所有的报刊编辑全都犯了大错。他们不理解我写作所具有的价值,也不明白选派具有中国阅历的人担任驻华记者的重要性。还好,他们并不代表全部,我的生活也不会被他们握在掌心。我靠自己就能回到中国。
我这么做了——1999年春,我买了飞往北京的单程票,并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头几个月,活儿很难找,可随后就有了,很快我就忙了起来。2000年,我放了几次长假,并且开始为《纽约客》和《国家地理》供稿。没过多久,之前回绝我的那些报刊给我来信,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太晚了。我喜欢自由地安排工作,选择自己的写作计划。怎么写中国,我有我的想法。曾经重要无比的四处求职被我抛在脑后。时至今日,我会永远感谢所有在1998年回绝了我的编辑们——回头看看,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棒的事情之一。
至今,《江城》已经出版了十多年。出版商很惊讶,它一直稳居美国畅销书榜,并将继续受到大众的欢迎。回首过去,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中国的时候,我的书恰好出版了。现在,很难想象还有编辑会说读者对中国话题不感兴趣。美国人一直有个问题,即对他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可中国是个例外。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现在有那么多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尤其高兴地看到,有很多美国青年开始学习汉语。《江城》往往是他们的阅读书目之一;我很欣慰,这本书有助于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介绍中国。
写《江城》的时候,我一直没太大的把握,涪陵人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我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最大的顾虑之一。书中绝大多数人物的名字我都做了改动,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我知道中国人对于自己在海外的形象比较敏感。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敏感——就我读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欢。我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但我拿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从头到尾,我在中国待了十年,写了三本书,还为各种杂志写了许多文章。但在那期间,我的作品几乎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对此,我无法释怀;专写某个地方的文章却只能让局外人读到,这似乎并不正常。反正,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书没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杂志上的文章也没能被翻译过去。
直至最近几年,这一切才得以改观。互联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人们把各种国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并贴到网上供大家阅读,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同时,中国的出版商也对外国作家日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年,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寻路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那是我的书首次在大陆地区亮相,我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它。同年春天,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答应做几场签售报告,并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我猜想,对于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他们不会有多大兴趣。
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旅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所参加的图书签售活动来者众多,我所遇到的读者敏锐而细心。总体而言,他们提出的问题比我在美国的类似场合要尖锐深刻得多。我发现,中国的读者对于书本身有共鸣,这让我颇感惊诧。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对三岔和丽水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产生兴趣,也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那些普通人——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
过去几年间,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感。我认为那反映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很多。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更渴望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番评价。跟我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比起来,他们对本书的共鸣更多了。当然,互联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跟外国人之间的个人接触也多了很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信心。说起《寻路中国》的受欢迎,我觉得这才是令我感到最高兴的事情。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接受方式,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聚焦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并且他们明白,没有人能够对中国做最后的断言。外国人的视角有用,中国人的视角同样有用。同理,倾听男性和倾听女性都非常关键。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总归是有用的。我希望我写的几本书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读懂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国度。
趁着那次旅行,我也回到了涪陵。跟我生活的那几年相比,这座城市扩大了一倍,在许多方面都变得难以辨认了。我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去重庆或者其他稍大一点的地方只能乘船,现在,涪陵开通了好几条高速公路和铁路。我曾经任教的学校从两千多名学生增加到了一万四千多,恰好反映了全中国高等教育的爆炸式发展。江河也变了样。我在书里写到的白鹤梁,寒冬时节露出水面,上面的题刻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现在,因为三峡大坝,白鹤梁被埋到了江面下一百三十英尺的地方。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些古老的题刻,因为该市修建了一座崭新的水下博物馆——耗资一亿三千二百万美元,这么大一笔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涪陵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城里的一些变化让我有点怀旧,甚至还有一丝伤感,因为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一去不返了。不过,最重要的精神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更生感激之情,感谢我曾有机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那里生活过。我相信,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涪陵是一个不寻常的地点——一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
李雪顺先生是我在涪陵期间曾经的同事,我要感谢他出色的翻译工作。我们力图让译本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本,只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动。如果有读者对本书以及我的其他作品感兴趣,可以点击www.peterhessler.net访问我的个人主页。
我永远感谢我在涪陵的朋友们,我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坦诚,如此耐心。我现在还跟将近一百个学生保持着联系,这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多年来,我看着他们长大成人,现在常常收到他们的学生写给我的信。我跟几位至交一直保持着联系,去年春天的重返涪陵之旅也让人兴奋不已。我无法预测,这座城市还将经历怎样的巨变,但我知道,它会永远是我的中国“老家”。
2012年1月写于埃及开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