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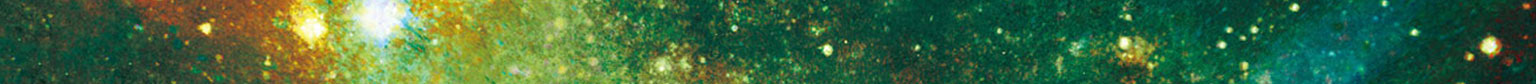
要是有这么一个地方,最好是靠海的地方,没有会议,没有斗争,也没有这么多的莫名其妙的麻烦事。带上几个学生,安安静静地搞项目搞研究,该多好。
束星北(1962年——时为极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分子)
几年前,我建过一个论坛,叫做繁星客栈,那里聚集了一些很不错的网友。有一天,一位网友转了一篇题为《一部浮夸的科学家传记——评刘海军〈束星北档案〉》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束星北档案》这本书,而且有可能也是我第一次听说束星北这个人。

束星北 |

束星北束星北档案》 |
那篇文章我虽只是粗略看了看,却留了一个印象。我曾看过不少国内作者撰写的华人科学家传记,比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苏步青、谢希德、“三钱”等的传记,可以说无一例外是高、大、全式的歌功颂德。有这样的体验做后盾,虽未看过《束星北档案》,见有人从浮夸的角度进行批评,倒也不觉意外。后来有一次回国,在书店里看到了《束星北档案》,想起那篇评论,便没有购买。
此后又过了很长时间,我几乎已将那本书忘了,不想却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里看到了它,于是借了回家。看完之后,我不无诧异地发现这本书在我读过的华人科学家传记中几乎可算是最好的(当然,这要部分地归因于其他传记的过于乏善可陈)。这本书虽的确对束星北的学术水平作了少许外行及浮夸的评价
 ,但重点并不在他的学术,而是在叙述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在全书30个章节(包括引言和尾声)中,与学术及教学有关的内容大都集中在前三章,比例极小。因此,尽管作者在讲述束星北的学术经历时,确实作出或引述过一些夸大其词的评价,但从内容比例上讲,这本书给人的真正印象并非是束星北是一个如何了不起的物理学家,而是他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的佝偻背影,以及他可怜可叹的人生悲歌,这与其他那些传记是截然不同的。
,但重点并不在他的学术,而是在叙述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在全书30个章节(包括引言和尾声)中,与学术及教学有关的内容大都集中在前三章,比例极小。因此,尽管作者在讲述束星北的学术经历时,确实作出或引述过一些夸大其词的评价,但从内容比例上讲,这本书给人的真正印象并非是束星北是一个如何了不起的物理学家,而是他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的佝偻背影,以及他可怜可叹的人生悲歌,这与其他那些传记是截然不同的。
从内容上讲,这本书最独特的地方,是它采用了大量的采访记录及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束星北本人所写的许多“思想汇报”。我之所以欣赏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此。事实上,在作者仰视传主及作者的学术外行性这些传统缺陷上,《束星北档案》与其他那些歌功颂德式的传记未必有很大差别,但该书采用的引述采访记录及档案资料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和淡化了那种缺陷。因为那些来自不同人、不同时期、不同视角的回忆资料大都很平实,其中有很多描述的是束星北的窘态(当然,外行人道听途说的过誉之词也是有的,但即便那样的回忆也并无刻意歌颂的意味,并且大都言明了是道听途说)。而束星北本人那“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的“思想汇报”,不仅没半点高、大、全的模样,反而充满了自我羞辱。有这些扎实的史料作基础,这本传记无论对于了解束星北这个人,还是了解当年那个吃了人还恬不知耻地让被吃之人歌颂自己的新社会,都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
。
好了,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束星北这个人。束星北出生于1907年,与那个让他受尽折磨的新社会有着共同的生日:10月1日,是中国物理界的一位前辈。束星北的求学经历相当奇特,美国学者胡大年在《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曾有一节用了“游学四方的束星北”作为标题。束星北在1924—1931这八年的求学期间,曾辗转于杭州之江大学(其校址在现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山东齐鲁大学(其校址在现山东大学医学院)、美国贝克大学(Baker University)、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Francisco)、德国汉诺威工业大学(University of Hanover)、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并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过硕士学位
 。束星北的这种奇特的求学史,看来体现了一种躁动的性格,他的同时代人吴大猷先生曾在《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一书中评论说束星北在欧洲和美国跑来跑去,没有认真地待在哪个地方做研究,他的学生许良英也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束星北缺乏专心致志的精神。束星北是一个有才之人,除物理外,在后来因生活所迫而改做的气象、化工乃至电器修理等工作上也都有不俗的表现,可惜却一生并无建树,究其原因,除不幸生活在一个特殊时代外,与他躁动的性格恐也不无关系。
。束星北的这种奇特的求学史,看来体现了一种躁动的性格,他的同时代人吴大猷先生曾在《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一书中评论说束星北在欧洲和美国跑来跑去,没有认真地待在哪个地方做研究,他的学生许良英也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束星北缺乏专心致志的精神。束星北是一个有才之人,除物理外,在后来因生活所迫而改做的气象、化工乃至电器修理等工作上也都有不俗的表现,可惜却一生并无建树,究其原因,除不幸生活在一个特殊时代外,与他躁动的性格恐也不无关系。
束星北1931年回国后,曾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暨南大学、浙江大学等地任教。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浙大遭到肢解,束星北选择了山东大学继续自己的教学生涯。1954年,束星北因公开反对马列主义统领一切的观点而遭批判,并被逐出物理系,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漫长噩运。离开物理系后,在竺可桢与王淦昌的关照下,束星北在山东大学气象研究室转行研究气象动力学,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十几篇论文。
但他这一短暂的庇护所也很快失守。1955年,气象研究室在“肃反”运动中被关闭,束星北夫妇遭到批斗和体罚,束星北一度萌生了自杀的念头。1956年,“鸣放”运动开始了,被这些风向迥异的政治运动搞得稀里糊涂的很多知识分子以为春天终于来临了,纷纷将前一阶段的苦水倒了出来,结果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在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中被一网打尽,这其中也包括束星北。
在“鸣放”期间,束星北发表了一些我个人非常欣赏的观点。在旁人——包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时候,束星北敏锐地看出了无论“肃反”还是“鸣放”,它们的主题虽截然不同,形式却如出一辙,全都充满了非理性和不守法的“人治”及“发泄”特点。1957年5月,束星北作了一次题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报告,主张推进法制。束星北的这种冷静和理性的思维,直到今天仍是中国社会相当欠缺的,因为直到今天,迎合大众胃口的谎言依然能轻易而迅速地调动巨大的非理性力量。
可惜,越是冷静和理性的思维对专制的威胁就越大。因此尽管束星北在“鸣放”期间的行为相较于激进人士来说显得很克制,但“反右”运动一降临,他很快就被戴上了“极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等帽子,于1958年10月与1800名其他右派一起被押往山东夏庄强制劳动。他们的劳动结果便是今天的崂山水库(当时叫做月子口水库)。在那里,劳动条件极其艰苦,工伤、自残和自杀时有发生;在那里,束星北吃尽了苦头,失尽了尊严。在1959年开始的那名为“自然灾害”,实为“大跃进”导致的三年人祸期间,他四处借贷,甚至不得已到田里去偷地瓜(结果被当场抓住)。

与此同时,他的所有子女都受株连,工作丢了,对象吹了,有的甚至被劳教。在这种无可抗拒的力量面前,束星北终于“顿悟”到螳臂挡车是没有出路的,并开始递交一些歌颂时局、自我改造的思想小结。随着水库工程的完工,束星北被遣到青岛医学院继续改造,当年的同事曾这样回忆这位经过改造的社会主义“新人”:
束先生是拄着拐杖来校报到的,他和几年前我见的那个神采奕奕、侃侃而谈、高声大嗓的先生已判若两人。要不是保卫科李科长在前面引着,我无法相信站在面前的这个憔悴、浮肿、目光散淡的老人就是束星北。他头顶着蓝色带护耳的棉帽,双手支在拐上,背抵在墙上,好像不这样“夹”着,人随时就会倒下去。李科长当着物理教研组全体成员给他训话时,他就像个泥塑木雕,身子和眼睛好长时间也不动一下。
但即便在这样的境况下,束星北仍然做出了一件一鸣惊人之事。1961年,他在干杂活之余,帮青岛医学院修好了一台损坏已久的进口脑电图机,引起了轰动。在那之后,青岛乃至外地的很多医院都慕名请他修理仪器。虽然修理仪器在束星北眼里只是雕虫小技,但自己重新变得有用还是鼓起了他的勇气,他开始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华来向党和人民“赎罪”,以便“摘帽”。为此他废寝忘食地努力着,并递交了“摘帽”申请。他的努力得到了一定层级的表扬,他心中的期盼也因此而变得更为炽热。青岛医学院公布第一批“摘帽”名单的那天,他拄着拐杖满怀希望地前往会场,可惜“摘帽”名单中并没有他。宣布完名单后,可怜的老先生茫然失措,痴痴地站在会场里直至人群散尽。

苦苦等待“摘帽”的束星北夫妇
受到沉重打击的束星北并不清楚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自己究竟怎样才能被“改造”好?他一方面更加努力,另一方面则以最诚恳的态度请大家给他提意见,甚至主动请求开一个针对他的评审会。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他的一再恳请下,“劳动人民”终于向他吐露了心里话。在评审会上,他听到了这样的批评:“你的书本知识有一些,志大才疏,但还高傲,你实际上还是个矮子”,“你老想从科研上找出路”,“你想单干,修仪器赚钱”。束星北的觉悟再低,到这时也基本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立场。“劳动人民”虽然缺乏知识,但并不缺乏忌妒心,想要凭借“劳动人民”所不会的技能来“摘帽”,那只会更让人家觉得他高人一等。束星北再次“顿悟”,要想让“劳动人民”满意,不能当专家,而必须当孙子。于是他自请长期打扫医学院所有的茅房,以彻底改造自己。
束星北打扫的不是五星级公厕,而是混杂了痰迹、粪便乃至人体器官碎片的医学院茅房,并且在打扫的过程中有时得用手去抠被这些东西堵塞的大便池,其情形是如今的我们不易想象的。他一边打扫,一边不断地提交思想汇报,在汇报中他写道:“刷茅房就是具体地听党的话,具体地为人民服务,因此刷茅房也就意味着刷掉资产阶级的臭思想”,他并且表示现在刷茅房还感觉到脏臭,今后的目标是要做到“完全自然,不感觉脏臭”。三个月后,他在思想小结中写道:“刷了三个月的茅房之后,越刷越起劲,越刷越愉快”。束星北所说的“越刷越愉快”倒不一定是谎话,因为干这样的活,“劳动人民”是不会找他麻烦的,这样干下去,说不定“摘帽”也会重新有望。人总是在希望中愉快,可惜的是,计划也总是赶不上变化,1965登场的“文化大革命”再次把束星北的希望抛进了深渊。
不过,对束星北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让他的“摘帽”希望再次落空,却也让他有幸脱离了焦点,毕竟,在这场更疯狂的运动中有更大、更刺激的鱼儿等待着革命群众去消遣。脱离了焦点的束星北渐渐无人问津,但他丝毫不敢怠慢,一丝不苟地执行着每天的改造任务。不过这时的他也开始偷偷读一些专业书,甚至趁扫雪的时候在雪地里写写公式。可是,脑子里的东西越多,无所事事的感觉就越折磨人。束星北是一个憎恶平庸,有着天才情结的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眼看着自己的年华在遥遥无期的平庸中一点点耗尽,他心中的焦虑也日益加剧,终于忍不住再次向组织发出了请求,他写道:
我今年已64岁,改造了十几年还没有改造好。岁月蹉跎,心中焦急:如果再过十几年,即使改造好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还能有什么用呢?……今后该怎么办,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谅解和容纳?……恳请党领导、军工宣队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之前,……(让我)回到人民内部,尽自己的力量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他的请求虽然恳切,却终究是不可能缔造奇迹的。后来的发展显示,他的真正出路,其实既不在于党和人民的“宽恕”,也不在于自己的“改造”,而在于外来的力量。这种力量终于来了:1972年10月,曾经是束星北学生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踏上了久违的故土,成为继杨振宁之后又一位穿越“文革”铁幕的海外物理学家。李政道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在会见他时请他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的断层问题做点工作。李政道表示,中国并不缺乏教育人才,而是没有给他们发挥才能的机会。作为例子,他说:“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
李政道不仅提到了束星北,而且还表示要见一见这位启蒙老师。这样的动静吓坏了山东医学院的“革委会”,他们以右派分子不能进京的规定为由阻止了束星北上京。但问题是,束星北不去北京,李政道会不会来青岛,甚至提出要到束星北家去坐坐呢?要知道,束星北的家可不是一般的家,据一位“革委会”的成员回忆,束星北的家是这样的:
那是我所见到的最赤贫破旧的家,你说它家徒四壁吧,破破烂烂的东西似乎又不少:缺了腿的桌子(晚上便铺上被子做床用),两个箱子(部队装子弹的箱子),几张自己打制的歪歪斜斜的板凳和一些堆得乱七八糟的书;地板虽是水泥的,可是到处都是裂缝,客厅中间还有一个大洞,大得能陷下腿去,上面盖着一张三合板,简直就是个陷阱。最不堪的是束星北的“卧室”,他的卧室不过是个两三尺宽的壁橱,束星北的个头这么大,常年“卡”在里面能舒服吗?“卧室”里只有一床被子,严格地说,那不是被子,只是一床破破烂烂的棉絮,如不是一些经经纬纬的黑色电工胶布粘连着,早就散了。
显然,这样的“教师之家”是万万不能让李政道看见的(万一李政道失足掉进那“陷阱”里,更是不堪设想)。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革委会”绞尽了脑汁,考虑了N种方案,比如让束星北火速搬入原党委副书记的家里,让束星北住进宾馆等,都感到不保险,最后干脆快刀斩乱麻,以束星北身体不适为由推掉了此事。
李政道没能见到束星北,便给他写了一封信:
束先生:
自重庆一别,离今已有差不多廿八年了。对先生当年在永兴湘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此次回国,未能一晤,深以为怅,望先生小心身体。
特此敬祝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生李政道上
李政道虽未能见到束星北,但他的惦念还是给束星北带来了生机。收到李政道的来信(这封信束星北连拆都没敢拆,第一时间就上交给了组织)后不久,束星北又鼓起勇气给组织写了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自1957年向党猖狂进攻之后,经过十多年的劳动改造,思想有所改变,……因之悔恨交加,亟思以实际行动来取得党和人民的宽恕与谅解,……特上牍恳求给我立功赎罪的机会……
一位如此弱小的学者,被迫承认向如此彪悍的党“猖狂进攻”,这实在很像是一则现代版的狼和小羊的寓言故事。幸好这党虽有一身横练功夫,却也有一个小小的练门,那就是特别器重外籍友人。束星北的待遇自李政道访华之后大为改善,他的“帽子”也终于在1974年被摘除,但他被“落实政策”则是在“文革”后的1979年,距离他被打成右派已有22年,距离他最早遭到批判则已隔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重返讲台的束星北 |

与老友王淦昌(右)在一起 |
“摘帽”后的束星北终于有机会重返讲台,但北大、厦大、暨大、中科院等依然不敢聘他,最后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破禁忌聘请了他,成为他一生最后五年的归宿。残酷的政治运动让束星北历尽苦难,却并未真正改变他。“文革”后,很多科学家加入了党员的行列,但当海洋所的领导希望束星北也递交入党申请时,却遭到了断然的拒绝。复出后的束星北又见到了昔日的同事及好友王淦昌,两位垂暮的老人竟像年轻时那样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临走时王淦昌感慨道:“你还是老样子。”束星北则回答说:“没办法,人是不可改变的。”
动荡的岁月终于过去了,可岁月留下的伤痕却再也无法抹去。晚年的束星北厌恶过去,避谈过去,却又时常陷入到过去的噩梦之中,难以自拔。他有时会忽然变得焦躁不安,梦游般地满屋子嚷嚷着寻找水桶、拖把和扫帚——那些都是他当年打扫茅房的工具。
束星北老了,在最后几年里,他拼命想把时间补回来,再完成些什么,那是他永不泯灭的天才情结所系,可惜一切已是镜花水月。1983年10月30日,这位际遇凄凉的前辈走到了生命之路的尽头。在去世前,他将自己的遗体捐给了青岛医学院,作解剖及制作骨骼标本之用。
束星北去世后,李政道、王淦昌、苏步青等著名学者发了唁电。束星北去世后的第三天,国家海洋局、青岛医学院及束星北的子女们举行了一个肃穆的遗体捐赠仪式。青岛医学院在遗体移交书上写道:我院对束星北教授这种献身精神表示敬佩。
但是,敬佩归敬佩,青岛医学院的很多人也正如束星北那样,是不可改变的。时势虽然变了,但每一次变迁都意味着风水可以轮转,权力可以重分,也意味着很多不可改变的人会投入新一轮的权力之争,因为那是他们永恒不变的兴趣。当然,每一次那样的争夺都师出有名,这一次的名目叫做“清除文革余孽”。等到硝烟散去、尘埃落定,终于又有人想起太平间里的束星北遗体时,已是半年之后的事了。人虽然不会变,遗体却是会变的,变得失去研究价值了。医学院的领导便遣两位学生将束星北的遗体送到一片荒凉的林子里去埋掉,而那两位学生嫌路太远,就近将遗体埋在了学校的篮球场边,那里如今立着一副双杠。
在那副双杠上锻炼的年轻学子们也许很少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双脚之下便是一位中国物理界前辈的埋骨之处。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写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