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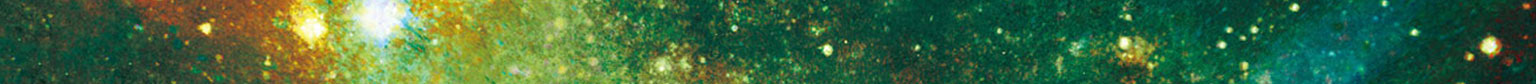
几星期前在书店闲逛时,发现美国物理学家苏士侃(Leonard Susskind)的 The Cosmic Landscape 一书被放在了特价区,惨遭贱卖(倒不是因为滞销,而是由于书的侧面不知怎的染上了一些黑色墨迹),于是毅然解囊买了一本。
苏士侃这本书是2005年底出版的,讲述的是他不久前做出的一项比较得意、且引起广泛兴趣及争议的工作。他这本书我以前曾买过一本送朋友,自己却未曾阅读,只记得书中所附的作者近照有点像《星球大战》(Star Wars)中的杜库(Count Dooku)——其实只是脸型和胡子有几分像,那是黑暗尊主(Dark Lord)的徒弟,是一个很厉害的坏蛋,曾砍去阿纳金·天行者(Anakin Skywalker)——也就是后来的黑武士达斯·维达(Darth Vader)——的右手(但最终还是被阿纳金·天行者所杀)。
苏士侃今年已经68岁,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理论物理学教授。他和获得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南部阳一郎一样,都是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不过与南部不同,苏士侃直到今天仍在与弦理论有关的领域中工作,并做出了不少有创意、且很能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工作——比如在黑洞与信息、弦景观(string landscape)与人择原理等方面的工作。不过,在这个以闲谈为主的“书林散笔”系列中,我们不谈太学术的话题,因此苏士侃的那些学术工作将留待今后再单独介绍。在本文中,我想讲述一段苏士侃在 The Cosmic Landscape 一书中提到的他本人亲身经历的有趣见闻。

|

|
苏士侃和他的 The Cosmic Landscape
这段见闻发生在苏士侃的年轻时代——确切地说是发生在他前往纽约曼哈顿北部的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就任助理教授的那一天。那时苏士侃已从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做完了一年的博士后工作。叶史瓦大学的那个职位是他当时手头的唯一职位。据他在 The Cosmic Landscape 中所述,这段经历发生在1967年,不过苏士侃的简历所列的叶史瓦大学任职时间却为1966—1970年,因此在时间上不排除有一年的误差。叶史瓦大学是一所私立的犹太人大学,创建于1886年,据说是美国最早的犹太人高等学府,2008年的全美排名是50。叶史瓦大学离我就读过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不远(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北5~6公里处),那里早年有很多犹太中产家庭居住,但后来逐渐变成了拉丁裔移民的聚居区。
曼哈顿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在曼哈顿的大学中,除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很小的校园外,其余大都只有一些被街道分隔开的建筑。苏士侃刚从康奈尔及伯克利那样环境优雅的校园来到这里,视觉上的反差是可想而知的。我以前住在曼哈顿的时候,曾多次路过曼哈顿南部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该校的建筑就分散在若干个街区。为了便于识别,那些建筑统一悬挂了青紫色的校旗,每次看到那些校旗,让我想起的不是大学,而是《水浒传》里那些小店门口迎风招展的酒旗。
不过对苏士侃来说,校园环境的好坏还在其次,因为更坏的事情很快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那天他来到叶史瓦大学的校区,在路人的指引下,找到了物理系。那是一间很小很昏暗的屋子,屋子里有一个大书架,书架上放满了大部头的书本,但不是物理书,而是希伯来文的古书。屋子里还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胡子灰白的家伙,正翻看着一本古书。
苏士侃的到来使宾主双方展开了历时一分钟的坦诚而富有建设性的会谈,那人向客人详细介绍了物理系的状况:
(1)他这间小屋就是物理系。
(2)他就是物理系的系主任。
(3)物理系有且仅有一位教授。
(4)那位教授就是他自己。
(5)他从未听说物理系招了助理教授。
在美国像这种“一人吃饱,全系不饿”的物理系其实并不罕见,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师兄就一度在那样一个物理系里工作过——当然,那意味着当过系主任。听完系主任的热情介绍,苏士侃的心沉到了海底——他还没上岗,看来就先要失业了。苏士侃当时虽然才26岁,却不仅已早早结了婚,而且还有两个小孩,这拖妻带幼的谋生,那是相当的不容易。但情势如此,夫复何言?他只得离开那皮包公司般的物理系,退回了街上。
幸运的是,在街上他碰到了一个熟人,于是他向那人叙述了自己的遭遇,那人听了哈哈大笑,说:“你想去的大概是研究生院的物理系,而不是本科的物理系吧。”笑罢,他告诉了苏士侃研究生院的地点。
苏士侃大喜过望,赶紧找到新地址。可到了那里——几个街区外的一个街口——一看,满眼皆是破烂店铺,有的甚至已经废弃,苏士侃再度失望。难道连朋友也会忽悠自己?他不死心地又在那街口转了一圈,结果突然在一家早已废弃的犹太婚宴店旁发现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Belfer Graduate School(贝尔夫研究生院)。那牌子指向一串楼梯,那楼梯污垢不堪,地毯也早已破旧,楼道里没有书香,却弥漫着食物的气味。看来这地方并不比那本科生的物理系强。
苏士侃硬着头皮登上楼梯,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厅,估计是那家犹太婚宴店昔日所用的舞池。大厅的四周约有二十来间办公室。看来这破烂小楼上的废弃舞池就是整个的研究生院了。不过,这时苏士侃看到了一件让他松了一口气的东西:黑板。在经历了方才的连番遭遇后,这小小的黑板在苏士侃的眼里变得亲切无比,简直就像救命稻草——用他自己的话说:“黑板意味着物理学家”。
但是,最让苏士侃振奋,并且让所有阴暗的氛围一扫而空的,则是人——几个正在黑板旁讨论问题的人。这是苏士侃这段见闻中最富戏剧性的地方,它大大出乎苏士侃的意料——当然,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几个参加讨论的人苏士侃全都认识,他们之中包括这样几位:
在这几位当中,芬克尔斯坦、阿哈罗诺夫、勒波维茨当时都在叶史瓦大学任教,彭罗斯和狄拉克则是访问学者。别看这地方寒碜,狄拉克早在1964年就莅临视察过,并且还发表过重要讲话,他的讲话内容后来被整理成了 Lectures on Quantum Mechanics ,是有约束量子理论的经典著作(该书有中译本:《狄拉克量子力学演讲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破旧小楼上的那几位物理学家是苏士侃在单一地点所见过的最杰出的一群物理学家,他们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他那一天的心情。只要有这些人在,哪里不能是物理系呢?那一天,那几位物理学家讨论的话题是真空能(vacuum energy),这个话题从此成为了苏士侃毕生探究的课题之一,这种探究最终导致了他这本 The Cosmic Landscape 的问世。
我记得几年前有很多人在讨论“大楼”与“大师”的问题。我想,苏士侃这段小经历对于那个话题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其实,在中国自己的教育史上,就有过一所没有半栋大楼,却有很多大师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那所大学只存在了短短八年,却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一页。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如果让中国的学人评选一所中国最杰出的大学,我想只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其中一个选项,它就一定会夺冠。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写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