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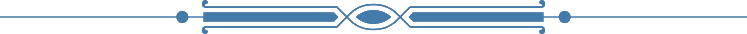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座很小的房子,用圆木修建而成,紧挨着“大宅”(黑人对主人住宅的通常称呼)。小屋前面有个小园子,经过精心地栽培和浇灌,每到夏天,草莓、木莓以及各色各样的水果蔬菜就长满了园子。小园子再往前,就是茂盛交缠的比格诺亚藤条和本地的多花玫瑰,蓊蓊郁郁一大片,就连挡着园子的圆木也被遮住了。在园子的一个角落里,到了夏天的时候,还有万寿菊、矮牵牛花和紫茉莉等鲜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所有这一切,都让克鲁伊大婶感到欣喜和自豪。
现在,让我们到小屋里面看看吧。今日大宅里的晚餐已经结束,克鲁伊大婶作为领班厨师准备好晚餐后,就把收拾碗筷等洗洗涮涮的杂活交给其他仆人,回到自己的安乐窝来给老头子烧饭来了。所以,这个在锅灶边忙碌的人,肯定是克鲁伊大婶了。她一会儿忙着在炖锅里炖什么东西,一会儿又像想起什么似的揭开了烤炉的盖子,顿时,一股香气冒出来,看来在烤的东西非常美味,正是她为茶点所做的小甜饼。她圆圆的脸庞,肤色黝黑发亮,光光亮亮的似乎涂了一层蛋清。她的头上戴着一顶浆得笔挺的无檐帽,那张丰润的脸上常常挂着一丝满意的笑容。我们得承认一点,对于这位方圆十里首屈一指的厨师来说,脸露得意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克鲁伊大婶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种天生厨师的神韵。一旦见她靠近,空地上的鸡、鸭和火鸡都会吓得魂飞魄散,它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克鲁伊大婶确实很高兴做这样的事情:把鸡或鸭的翅膀绑紧到身上,再往鸡或鸭的肚子里塞各种各样的配料,然后或烹或烤。而这一切手段,怎能不让那些感觉敏锐的家禽胆战心惊呢?而她做的玉米饼也是花样繁多,像锄形饼、多角饼、松饼,还有其他各种编了名目的饼,让有些资历浅的厨子看了,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有客人到来、置办宴席,常激发克鲁伊大婶产生无穷的创造力和活力。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堆在门廊的一排排旅行箱更让她兴奋了。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她又可以大展身手,再创佳绩了。
这会儿,克鲁伊大婶正向平底锅里认真端详着。就让她暂时沉浸于自己的快乐吧,趁这个机会,我们仔细地瞧一瞧他们家的小屋吧。
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床,上面铺着一条洁白的床单。床边铺着一块大小合适的地毯。克鲁伊大婶站在地毯上,说明在这个庄园里她的地位可不低。地毯、床铺和这个小角落,都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而且如果管得住的话,这个小天地是不容那些小机灵鬼胡闹的。事实上,这个角落算是这个家庭的客厅了。而在屋子的另一角,也摆着一张床,相比之下粗陋得多的了,显然是他们家平常使用的。壁炉上面的墙上贴着几幅《圣经》插图,旁边还挂着一幅华盛顿将军的肖像,那色彩和技法,如果将军有幸亲眼得见,肯定会目瞪口呆。
还有一个角落有一张长凳,上面正坐着两个鬈发男孩,他们都有着晶亮发光的黑眼睛和圆润的小脸蛋。这时,他们正在忙着教一个小宝贝儿学走路。正像其他的小小孩一样,这个小家伙站了起来,晃晃悠悠地往前走,没走几步,就一跤跌倒在地。她接二连三的失败却受到了热烈的喝彩,那些人好像是在观看什么精彩演出似的。
壁炉前面摆着一张桌子,桌腿怎么放也不平稳,就像得了风湿病一样,桌子上面铺着一张桌布,摆放着有着图案漂亮、颜色明丽的茶杯托盘。别的一些迹象也表明,晚餐就要开始了。桌子旁边坐着谢尔比先生最得力的仆人汤姆。他会是本书的主人公,所以我们要向读者仔细介绍一下他。他身材魁梧,胸膛阔阔的,看起来很强壮;黝黑的皮肤发出亮光,他的脸庞是典型的非洲人那样的,而他脸上的表情常常严肃而稳重,同时又流露出天性的善良和仁慈。他的神态表现出自尊自爱,不过也显示出对待他人有一种坦诚的品格,还有忠厚和纯朴的气质。
这时他正在小心翼翼地往面前的石板上慢慢地抄写字母。十三岁的小少爷乔治站在旁边指导着他。乔治聪明帅气,看来他满心享受着当老师的感觉。
“不是那样写法,汤姆叔叔,不是那样写法。”看到汤姆把g的尾巴拐到了右边,乔治喊道,“看,你那样写就成q了。”
“哟,是吗?”汤姆应道。看着自己的小老师轻轻松松地在石板上写了很多g和q,汤姆不禁既佩服又羡慕。接着,汤姆用粗大的手指握住笔耐心地练习起来。
“白人就是灵巧啊!”克鲁伊大婶说。她充满欣赏地赞美着小主人,看了一会儿,又去拿叉子叉了一块腊肉来,往平底锅里抹上油,“你瞧他写字时多轻松!他还认识很多字,每晚读书给我们听,真是太有趣了。”
“不过,克鲁伊大婶,我现在觉得很饿,你锅里的饼是不是快烙好了呢?”乔治说道。
“快了,乔治少爷,”她掀开锅盖朝里看了一眼,“烙得黄焦焦的,颜色真好看。烙饼的事儿就交给我吧。那天,太太让莎莉试着去烙饼,她说:‘嗯……让莎莉去试一下。’我说:‘算了吧,她会把好好的粮食全给糟蹋掉的,那可就太可惜了。她那饼烙得坑坑洼洼,就像我的鞋子一样难看。我看,她以后还是别再烙饼了。’”
贬了一下莎莉还不成熟的技术之后,克鲁伊大婶掀开了锅盖,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烙得齐整光洁的油饼,这正是城里的糕点店争相抢购的上等品。显然,它将成为款待客人的主力食品。现在,克鲁伊大婶开始认真地张罗起晚饭来。
“嘿,莫思,贝特!快让开路,你们这些小鬼。走开,波莉,妈妈的小心肝儿,我会尽快给宝宝弄东西吃的。乔治少爷,请拿走这些书,坐下来陪着那个老头子,我马上把香肠和刚出锅的烙饼给你们送过来。”
“他们叫我回大宅子吃晚饭,不过,我知道在哪儿能吃到好吃的饭菜。”乔治说。
“宝贝儿,你知道就好。”克鲁伊大婶说着,把热气腾腾的烙饼放在了乔治的盘子上,“你知道大婶我呀,会把最好吃的留给你。你就独自在这儿享用吧,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说完,她开玩笑地用手指头碰了一下乔治,很快又回到烤炉那儿忙活开了。
“现在吃饼喽!”看克鲁伊大婶确实忙不过来,乔治喊了一声,然后抓起一把大刀,往烙饼上面砍了下去。
“我的天哪,乔治少爷。”克鲁伊大婶急忙抓住乔治的胳膊,“不能用这么大的刀切烙饼!会把饼上面涂的东西毁掉的。得用这把薄点儿的刀,我把它磨得很快,是专用来对付烙饼的。看,这样很容易就把饼切好了。来,赶快吃吧。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好吃了。”
“汤米·林肯说,他家的詹妮厨师比你手艺高。”嘴里塞满烙饼的乔治,嘟嘟囔囔地说道。
“林肯家的人手艺一点儿都不高!”克鲁伊大婶一脸鄙夷地说,“要是跟我们全家比手艺,也许还算说得过去。他们的风度、气派却不能和我们相比。就拿林肯先生和我家老爷来比吧,还有林肯太太,她进门时,哪有我家太太的派头?去他的吧,别提林肯这家人了!”克鲁伊大婶摇着头,好像在这个世上,有人希望她不知道什么事似的。
“噢,但我也听你说过詹妮的厨艺不错!”乔治说道。
“我以前或许说过这话,”克鲁伊大婶说,“她做家常饭还行,玉米面包也做得不错,马铃薯和玉米糕点还说得过去,但至少现在她做饭不太好,以前詹妮做的玉米糕还算可以,但她怎么会烹调高档的食品?她可以让肉馅儿饼的表面带上光泽,不过那馅儿饼皮又是怎样的?她能发出松软的面吗?她做出的饼能看起来像一朵飘着的云,入口即化吗?我看过詹妮为玛莉小姐的婚事做的喜饼。你知道,我和詹妮是好朋友,我没说过她的坏话。但是,乔治少爷,如果是我做出了那样一堆饼,恐怕会整个星期都睡不好觉的。那是怎样的喜饼啊!”
“我想,詹妮自己会觉得她做的喜饼还不错呢!”
“她当然感觉良好,不是吗?她还向我夸耀过自己的手艺呢,你知道吗?问题就出在这儿。詹妮不知道自己的手艺到底怎样,她的主人也不怎么样,她怎么能指望从主人那儿得到指点呢?所以责任不在詹妮。啊,乔治少爷,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克鲁伊大婶叹息着,眼睛动情地不停眨巴着。
“克鲁伊大婶,我明白着呢,我吃的馅儿饼和布丁是最好的。”乔治说,“不信你可以去问汤米·林肯,每次我碰到他,都会夸耀我在家中所享受的好福气呢。”
小主人的几句玩笑话逗得克鲁伊大婶哈哈大笑,她仰靠在椅背上,直笑得眼泪顺着黑色的脸庞滚下来。一会儿,她用手拍了拍乔治,一会儿,她又用手指戳了戳他,让他走开,说,不然总有一天会要了她的老命的。她一边说着这样的残酷预言,一边仍然笑个不停,一次比一次长久、欢快,直搞得乔治也感到自己真是一位危险人物,他今后要小心说话,再也不能胡言乱语了。
“你真对汤米这样说了吗?老天,你们这几个小鬼还真敢吹啊!你对汤米吹嘘了,是吗?乔治少爷,你这样做不怕人笑话吗?”
“是的,”乔治说,“我这样对他说:‘汤米,你真该去看一看克鲁伊大婶做的,什么才叫真正的馅儿饼。’”
“很遗憾,汤米不会看到的。”克鲁伊大婶说。看来,汤米对馅儿饼的无知已经深深地刻进她那善良的心灵了,“乔治少爷,你应该让他来我家吃顿饭,保证会让你有面子。不过,乔治少爷,你要永远记住,我们的一切福分都源自上帝,所以不要因为吃到好馅儿饼而自以为了不起啊。”克鲁伊大婶神情严肃地说。
“好啊,我下个星期约他来家里玩儿,”乔治说,“克鲁伊大婶,你要拿出全部本事来,我们要让他吃完这顿饭,过半个月还咂巴嘴,好不好?”
“当然,这样最好了,”克鲁伊大婶兴奋地说,“你就等着吧。老天,想想我以前操办过的宴席,那是多风光!还记得那次科诺克斯将军来时,我为他准备的鸡肉馅儿饼吗?那次,为了馅儿饼皮,我和太太差点儿就吵起来。我真不懂太太在想什么。你负着准备宴席的重大责任,忙得转不开身,但她们非要插上来,就在你身边转啊转的。那天也是这样,太太一会儿让我这样干,一会儿又要求我那样干,最后我不得不出言顶撞太太了。我说:‘太太,请看看您那白嫩的双手、手指上戴的金戒指,就像我种的白色合欢花一样美丽;再看看我这双粗黑的双手,难道您不明白,您待在客厅,我来做馅儿饼,这才是上帝的安排吗?’啊,乔治少爷,那天我是这样莽撞。”
“妈妈说什么了呢?”乔治问。
“说什么?她笑眯眯地回答说:‘啊,克鲁伊大婶,我想你说得很对。’然后她就回到客厅去了。我是那样无礼,按说她本该敲碎我的脑壳才对。但话又说回来,有小姐、太太在厨房,我可真是不知道怎么干活儿了。”
“嗯,那顿饭做得很棒——我记得每个人都这么说。”乔治说。
“我不也这么觉得吗?那天我不是躲在餐厅后面吗?我不是亲眼看着科诺克斯将军三次要求添馅儿饼吗?我还听他说:‘谢尔比太太,您家厨师的手艺真是不俗啊!’天哪,当时我听了简直欣喜若狂了。”
“将军对烹调也是真在行呢,”克鲁伊大婶伸直身子,得意地说,“他是个好人!他是弗吉尼亚一个古老家族的孩子,他就像我一样识货。乔治少爷,馅儿饼有很多种样式,每种的风味都不一样。你知道吗?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将军那样懂行,可以品出不同的味道。他了解其中的奥妙,从他说的话里就能听出他是这方面的行家。”
这时,乔治少爷已经再也吃不下一口饭了,这是一个孩子能撑得下的最大饭量(在特别的情况下)。直到现在,他才顾得上注意到屋子角落里那几个长着鬈发、眼睛乌黑发亮的小脑袋。他们眼巴巴地看着小少爷吃饼,他们的口水都流了一地了。
“嘿,莫思,贝特,”乔治把烙饼掰成一块块,向他们扔过去,“你们也想吃,是吗?克鲁伊大婶,再给他们烙几张饼吧。”
乔治和汤姆走到壁炉边一个舒适的座位上坐下来,克鲁伊大婶已经烙好了一大堆馅儿饼。她把孩子抱在膝头上,不时往自己和孩子的嘴里塞着饼,同时还不忘分神把饼给莫思和贝特吃。这两个小鬼更喜欢一边吃着饭,一边在桌子下面打滚逗趣,时不时还揪一揪小妹妹的脚指头。
“靠边去,快点儿,”当孩子闹得太凶时,母亲一边呵斥,一边朝桌底下踢着,“难道你们没看到家中有白人客人吗?都给我放规矩点儿,都老实点儿,好吗?要是不听话,等乔治少爷走了之后,看我不扯住你们的袖子,给你们好一顿揍!”
很难说清这种恐吓究竟有什么意思,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看似可怕的警告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孩子们听了无动于衷。
“啊!”汤姆叔叔说,“真是皮厚发痒的家伙。要是一天不打,他们就浑身不自在。”
此时,这群小家伙从桌子下面爬出来,搂住母亲怀中的孩子猛亲着,弄得孩子手上、脸上满是黏糊糊的糖浆。
“快走开!”母亲一把推开那几个毛茸茸的小脑瓜,“整天胡闹,乱成一团,搅和得分都分不开了,快去用水把自己洗干净。”说完,她又使劲儿地拍了他们一巴掌,这让孩子们又大笑起来,他们大嚷大叫着跑到门外去了。
“你见过有这么淘气的孩子吗?”克鲁伊大婶无奈又骄傲地说,然后拿出一条专门应付这种突发事件的旧毛巾,从破茶壶中倒出一点儿水淋在毛巾上,开始擦拭小家伙脸上和手上的糖浆。擦干净后,便把小家伙放到汤姆叔叔怀里,她自己就忙着收拾锅碗瓢盆去了。那个小家伙拉了一下汤姆叔叔的鼻头,又抓了一把他的脸,还把胖乎乎的小手放在汤姆叔叔的鬈发上揉啊揉,看来她还是比较喜欢最后一项工作。
“她很神气,不是吗?”汤姆叔叔说着,伸直胳膊把孩子放远一点儿,以便仔细瞅一瞅这个小宝贝儿。然后,他让孩子骑在他宽阔的肩上,带着她一起跳起舞来,而乔治少爷这时候也拿着手帕逗她玩儿。刚刚进屋的莫思和贝特也跟在妹妹后面像熊一样叫着,直到克鲁伊大婶喊着说他们的大喊大叫会让小妹妹的头搬家时,他们才停止吵闹。据克鲁伊大婶介绍,这种“外科手术”在这里就是家常便饭。她的喊声并没有制止孩子们的欢叫,他们唱着、跳着、翻滚着,直到觉得尽兴了,才安静下来。
“好了,拜托你们别再闹啦!”克鲁伊大婶一边说着,一边从大木床下拉出一张做工粗糙的小床,四个床脚下面还装上了轮子,“好了,莫思,贝特,你们都给我上床,我们马上就要祷告了。”
“噢,妈妈,我们也要看祷告会,肯定很有意思,我们都不想睡觉。”
“哦,克鲁伊大婶,把小床推进去,就让他们看一会儿吧!”乔治少爷果断地说,同时推了一下小床。少爷的话让克鲁伊大婶觉得很体面,于是她高兴地把小床推了进去,说:“好吧,看看也许对他们也有好处。”
这时,房间里的人都聚在了一起,讨论着会场的安排和布置事宜。
“我可没办法一下子弄那么多椅子。”克鲁伊大婶说。相当长时间以来,每星期的祷告会都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举行,缺少椅子是经常的事儿,不过大家觉得,这次的椅子问题也是会解决的。
“上星期演唱时,老彼得叔叔把那张旧椅子的腿给压断了。”莫思说。
“得了吧,小鬼头,我看准是你把椅子腿给拆了吧。”
“嗯,如果靠墙放着的话,那把椅子还是不会倒的。”莫思狡辩道。
“那把椅子不能让彼得叔叔坐,因为他唱歌的时候老喜欢挪地方。那天晚上,他差不多从屋子这头转到屋子那头了。”贝特说。
“上帝啊,就让他坐在那上面吧,”莫思说,“等他唱道:‘圣徒们、罪人们,来吧,请听我说。’然后他就会一屁股摔在地上。”莫思很形象地模仿着老彼得的鼻音和老人倒地的样子,像是预演一场将要发生的恶作剧。
“啊呀,难道你不能规矩点儿吗,就不能知点儿羞吗?”克鲁伊大婶说。
但乔治少爷和这个冒犯者一起哈哈大笑,还大声称赞他是个不简单的小滑头。看来,母亲的警告再次失灵了。
“哎,老家伙,你去把那两只大桶搬进来。”克鲁伊大婶说道。
“就像乔治少爷读的圣书里那个寡妇的坛子一样,妈妈的大桶没有一次失灵。”莫思侧过脸,对贝特说。
“我敢肯定,上个星期有一只桶瘪了,”贝特说,“就在大家唱到一半时。难道那次不算失灵吗?”
在莫思和贝特说话的时候,汤姆叔叔已把那两只大空桶推了进来。为了不让它来回滚动,两边都放上了大石块。大家在桶上放好木板,又把几只盆和水桶倒放在地上,再加上那几把破椅子,最后,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
“乔治少爷的书读得真好,我知道他会留下来为我们读圣书的,”克鲁伊大婶说,“那样会给祷告会增添不少乐趣。”
乔治立刻答应了,只要被器重,哪个孩子会拒绝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呢?
很快,小屋里就挤满了人,既有八十岁的白发老人,又有十五六岁的姑娘小伙。他们随意地扯了一会儿闲话,例如,“塞莉大婶从哪儿搞来一条红头巾”“太太打算在做好罗纱衣裳后,就把那件平纹布外衣送给莉兹”“谢尔比老爷打算买匹栗色马驹,这又会为此地增添不少风采”,诸如此类的话题。有些得到主人允许的邻近人家的仆人也赶来参加祷告会。他们带来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消息,比如,庄园里的人说什么了,做什么了。在这里,人们可以天南地北自由地谈论,就像上流社会的人在谈论那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样。
不一会儿,唱念开始了,在场的人都很兴奋。那与生俱来的清脆嘹亮的嗓音并没有被鼻音掩盖。所唱的歌曲大都是附近教堂常常听到的有名圣歌,还有一些是从野外布道会上听来的较粗犷热烈的曲子。
其中一首歌的合唱部分充满了活力和热忱,歌词是这样的:
战死在沙场,
战死在沙场,
我的灵魂闪耀着光芒。
另一首他们喜爱唱的歌中,经常重复这样的歌词:
啊,我要去天国——你不愿伴我同行吗?
你没看到天使在向我招手,深情地把我呼唤?
你没看到那金色的城市和永恒的时光?
还有些曲子里经常提到“约旦河岸”“迦南战场”和“新耶路撒冷”这样的字眼。黑人们生来感情丰富,富于联想,他们经常让自己沉浸于赞美诗和触动人心的妙语中。唱歌的时候,他们时而欢笑,时而痛哭,时而互相击掌,时而悠然握手,那情景仿佛他们已经抵达约旦河彼岸。
和歌声交织在一起的,是人们在相互劝诫以及倾诉各自对灵性的感受。一位已经老得不能干活儿的白发老妇深受大家的爱戴,她拄着拐杖站起来,“孩子们,我很高兴,因为我再一次见到了你们,听到了你们的歌声,因为说不定哪天我就撒手而去了。我已经收拾好包袱和帽子,早已为踏上天国之路做好了一切准备。孩子们,我想说,”她用拐杖用力地敲了敲着地板,接着说,“天国是那样伟大,那是一块神奇之地,美妙无比啊!”
老妇人激动不已,老泪横流。于是大家唱道:
啊,迦南,光明的迦南,
我是那样热切地向往着你。
应大家的邀请,乔治少爷诵读了《启示录》的最后几个章节。诵读时不时被人们的赞美之词打断。“真是了不起!”“听他念得多优美啊!”“真是不可思议!”“那会是真的吗?”大家不停地插嘴。
聪明的乔治对宗教的理解与认识,主要得益于母亲的教导。听到众人对他的赞美,他更不时在庄重的诵读中加进自己的解说,这更加让年轻人觉得羡慕,并得到了年长者的祝福。大家公认:“乔治念得比任何一个牧师都好。”“真是不可思议。”
在宗教事务方面,汤姆是众人公认的“主教”。他善于组织活动,人品很好,再加上他的胸襟和教养比别人高出一截,所以大家都把他当成自己的牧师来尊敬。他做的祷告特别生动感人,富有孩子般天真的痴迷,另外,他会用《圣经》的语言来祷告,这样更是独具一格,是别的祷告风格所不能比拟的。他对经书的理解也非常透彻,仿佛经书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似的,祈祷时,他往往能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用一位老黑奴的话来说,汤姆的祈祷和天堂的福音一样。因此,汤姆叔叔祷告时的声音常被周围听众们虔诚的应对声打断。
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然而,在主人谢尔比先生的大宅,却呈现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
奴隶贩子和谢尔比先生坐在餐厅里一张小桌子旁,桌上摆放着一些契约和书写用具。
谢尔比先生忙着数那几沓钞票,点完后,他把钞票递给奴隶贩子,奴隶贩子也照样点了一遍。
“钱数没错,现在请在这契约上签字吧。”奴隶贩子说。
谢尔比先生把契约拿过来,在上面签了字,就匆忙丢开手,像在做某件不愉快的事一样。接着,他把契约和钞票推到奴隶贩子面前。赫利从一个旧提包里取出一张羊皮纸文件,看了看,然后把它递给了谢尔比先生。谢尔比先生急忙接过文件。
“好,现在这事儿完结了!”奴隶贩子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
“完结了!”谢尔比先生以沉思的口气说,又深吸了口气,接着又说道,“完结了!”
“好像你对这笔生意不大满意啊。”奴隶贩子说。
“赫利,”谢尔比先生说,“你要答应我在弄清楚买主的身份前别卖汤姆。你要以你的名誉起誓。”
“哦,这样的事,你刚才不是做了吗?”奴隶贩子说。
“你知道,我这是被逼无奈了。”谢尔比先生严厉地说。

“那你也要明白,我或许也会有被逼无奈的一天哪。”奴隶贩子说,“不过,你别担心,我是不会虐待他的,还会尽可能帮他找个好主人。要是有什么事情值得我感谢上帝的话,那就是,我从来不是个狠心肠的人。”
尽管奴隶贩子已经说明了他的人道主义原则,但谢尔比先生还是不太相信他的话,最好的安慰也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他无声地打发走了奴隶贩子,接着点燃雪茄,独自抽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