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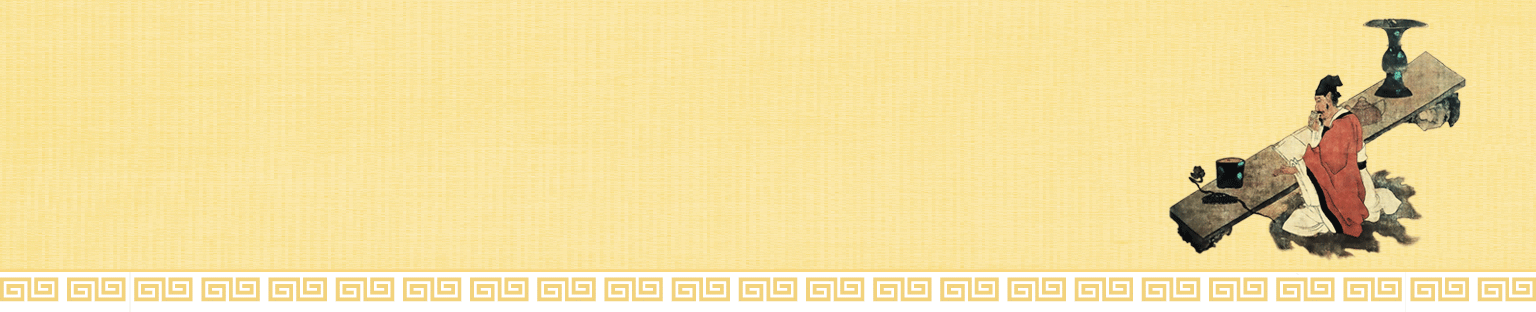
公孙龙
 ,六国时辩士
,六国时辩士
 也。疾
也。疾
 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
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
 ,为“守白”
,为“守白”
 之论。假物取譬
之论。假物取譬
 ,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
,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
 马也。
马也。
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名
 色,言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
色,言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
 ,形非色也。夫言色则形不当与
,形非色也。夫言色则形不当与
 ,言形则色不宜从
,言形则色不宜从
 。今合
。今合
 以为物,非
以为物,非
 也。如求白马于厩
也。如求白马于厩
 中,无有,而有骊色
中,无有,而有骊色
 之马,然
之马,然
 不可以应有
不可以应有
 白马也。不可以应有白马,则所求之马亡
白马也。不可以应有白马,则所求之马亡
 矣,亡则白马竟非马。欲推是辩
矣,亡则白马竟非马。欲推是辩
 ,以正名实
,以正名实
 ,而化
,而化
 天下焉。
天下焉。

公孙龙,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擅长名实之辩的人物。他厌恶当时名实关系的混乱现象,凭借自己禀赋所长,提出了“白马非马”的“守白”之说。并借着可直观的事物打比方以喻说道理,来为“守白之说”辩难,称白马不等同于马。
所谓白马不等同于马的道理在于:称“白”是来说明颜色的,称“马”是来说形体的。颜色不等同于形体,形体也不等同于颜色。说颜色就不该让形体参与其中,说形体也不宜带上颜色。现在把颜色和形体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对的。譬如要在马棚里找白马,恰巧没有,而只有黑色的马,这样就不可以说这里有白马。既然不可以说有白马,那么就是要找的对象没有了;既然要找的对象没有了,所以白马毕竟异于马。他想把这样的论辩推广开来,并根据这一原理来端正名实关系,从而教化天下的人。
龙与孔穿
 ,会赵平原君
,会赵平原君
 家。穿曰:“素闻先生高谊
家。穿曰:“素闻先生高谊
 ,愿为弟子久,但不取
,愿为弟子久,但不取
 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
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
 此术,则穿请为弟子。”龙曰:“先生之言悖
此术,则穿请为弟子。”龙曰:“先生之言悖
 。龙之所以为名
。龙之所以为名
 者,乃以白马之论尔。今使龙去之,则无以教
者,乃以白马之论尔。今使龙去之,则无以教
 焉。且欲师之者,以智与学
焉。且欲师之者,以智与学
 不如也。今使龙去之,此先教而后师之也。先教而后师之者,悖。且白马非马,乃仲尼之所取。龙闻楚王张繁弱之弓
不如也。今使龙去之,此先教而后师之也。先教而后师之者,悖。且白马非马,乃仲尼之所取。龙闻楚王张繁弱之弓
 ,载忘归之矢
,载忘归之矢
 ,以射蛟、兕
,以射蛟、兕
 于云梦之圃,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
于云梦之圃,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
 。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
。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
 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
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
 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先生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学而使龙去所教,则虽百龙
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先生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学而使龙去所教,则虽百龙
 ,固不能当前
,固不能当前
 矣。”孔穿无以应焉。
矣。”孔穿无以应焉。

公孙龙在赵国平原君家中会见孔穿。孔穿说:“我一向听说先生的义理高深,早就想做先生的弟子了,只是未敢苟同先生‘白马非马’的理论,希望放弃这套理论,我便俯首甘拜为弟子。”公孙龙说:先生的话未免荒谬了,我之所以能为人所知,靠的是“白马非马”之说,现在要我放弃它,那我就没有什么可以施教于人的了。而且要拜人为师的,总是因为才智和学识不如人家吧,现在你让我放弃“白马非马”的学说主张,这是先施教于我然后以我为师。先施教于人而后以人为师,这是于理相悖的。“何况‘白马非马’的论旨还是您先祖仲尼所认可的。我听说当年楚王曾经拉着‘繁弱’强弓,搭上‘忘归’利箭,在云梦泽园林射猎蛟龙犀牛,但是不慎把弓弄丢了,随从们请求去把弓找回来,楚王说:‘楚国的国王丢了弓,也是楚国的人捡到的,又何必去找呢?’仲尼听到这件事时便说:‘楚王这样似乎讲仁义了,但还不够。应该说:人丢了弓,人捡到就是了,又何必限定是楚国的人呢?’由此看来,您的先祖仲尼是把‘楚人’与‘人’区别开来的。既然肯定了仲尼把‘楚人’与‘人’区别开来的说法,却反非难我把‘白马’与‘马’区别开来的主张,这是于理相悖的。“您既然信奉儒家学说,反而否弃仲尼所采认可的主张,既又想跟我学习却又叫我放弃我能教你的东西,这样,即使有百倍贤能于我的人,也一定无法当着您的面把道理说清楚啊”孔穿无言以对。
公孙龙,赵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叶
 也。穿与龙会,穿谓龙曰:“臣
也。穿与龙会,穿谓龙曰:“臣
 居鲁,侧闻下风
居鲁,侧闻下风
 ,高
,高
 先生之智,说
先生之智,说
 先生之行,愿受业
先生之行,愿受业
 之日久矣,乃今得见。然所不取先生者,独不取先生之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白马非马之学,穿请为弟子。”公孙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学,以白马为非马者也。使龙去之,则龙无以教。无以教而乃学于龙也者,悖。且夫欲学于龙者,以智与学焉为不逮
之日久矣,乃今得见。然所不取先生者,独不取先生之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白马非马之学,穿请为弟子。”公孙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学,以白马为非马者也。使龙去之,则龙无以教。无以教而乃学于龙也者,悖。且夫欲学于龙者,以智与学焉为不逮
 也。今教龙去白马非马,是先教而后师之也。先教而后师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龙者,似齐湣王之谓尹文
也。今教龙去白马非马,是先教而后师之也。先教而后师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龙者,似齐湣王之谓尹文
 也。齐湣王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齐国无士,何也?’尹文曰:‘愿闻大王之所谓士者。’齐湣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
也。齐湣王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齐国无士,何也?’尹文曰:‘愿闻大王之所谓士者。’齐湣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
 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
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
 则顺。有此四行
则顺。有此四行
 ,可谓士乎?’齐湣王曰:‘善。此真吾所谓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为臣
,可谓士乎?’齐湣王曰:‘善。此真吾所谓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为臣
 乎?’王曰:‘所愿而不可得也。’是时齐湣王好勇
乎?’王曰:‘所愿而不可得也。’是时齐湣王好勇
 ,于是尹文曰:‘使此人广庭大众之中,见侵侮而终不敢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钜
,于是尹文曰:‘使此人广庭大众之中,见侵侮而终不敢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钜
 士也?见侮而不斗,辱也!辱则寡人不以为臣矣。’尹文曰:‘唯见
士也?见侮而不斗,辱也!辱则寡人不以为臣矣。’尹文曰:‘唯见
 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也。然而王一以为臣,一不以为臣,则向之
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也。然而王一以为臣,一不以为臣,则向之
 所谓士者,乃非士乎?’齐湣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君,将理
所谓士者,乃非士乎?’齐湣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君,将理
 其国,人有非则非之,无非则亦非之;有功则赏之,无功则亦赏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齐湣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窃观
其国,人有非则非之,无非则亦非之;有功则赏之,无功则亦赏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齐湣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窃观
 下吏之理齐,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国,信
下吏之理齐,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国,信
 若先生之言,人虽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
若先生之言,人虽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
 未至然
未至然
 与?’尹文曰:‘言之敢无说
与?’尹文曰:‘言之敢无说
 乎?王
乎?王
 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见侮而终不敢斗,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斗者,辱也。”谓之辱,非之也。无非而王非
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见侮而终不敢斗,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斗者,辱也。”谓之辱,非之也。无非而王非
 之,故因除其籍
之,故因除其籍
 ,不以为臣也。不以为臣者,罚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且王辱不敢斗者,必荣
,不以为臣也。不以为臣者,罚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且王辱不敢斗者,必荣
 敢斗者也。荣敢斗者,是(之也。无是)而王是
敢斗者也。荣敢斗者,是(之也。无是)而王是
 之,必以为臣矣。必以为臣者,赏之也。彼无功而王赏之。王之所赏,吏之所诛也;上
之,必以为臣矣。必以为臣者,赏之也。彼无功而王赏之。王之所赏,吏之所诛也;上
 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赏、罚、是、非,相与四谬
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赏、罚、是、非,相与四谬
 ,虽十黄帝
,虽十黄帝
 ,不能理也。’齐湣王无以应焉。故龙以子之言有似齐湣王。子知难白马之非马,不知所以难之说。此犹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类
,不能理也。’齐湣王无以应焉。故龙以子之言有似齐湣王。子知难白马之非马,不知所以难之说。此犹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类
 。”
。”

公孙龙是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孔穿是孔子的后裔。孔穿拜会公孙龙,便说:“鄙人住在鲁国,在下边久仰先生的声名,羡慕先生的才智,钦佩先生的德行。早就想从师于先生,今天才有幸拜见。只是不敢苟同您那白马异于马的学说,请您放弃的主张,我就情愿为您的弟子。”公孙龙说:先生的话未免荒谬了,我之所以能为人所知,靠的是“白马非马”之说,现在要我放弃它,那我就没有什么可以施教于人的了。而且要拜人为师的,总是因为才智和学识不如人家吧,现在你让我放弃“白马非马”的学说主张,这是先施教于我然后以我为师。先施教于人而后以人为师,这是于理相悖的。“先生用以施教于我的东西,有点像齐湣王对尹文所说的那样。齐湣王曾对尹文说:‘我很喜爱士人,可是齐国没有士人,怎么办?’尹文说:‘想知道大王所谓士的标准是什么?’齐湣王一时说不上来。尹文接着说:‘现在有这样一个人,事奉君主很忠诚,奉侍父母很孝敬,结交朋友很诚实守信,对待乡亲很平易和顺,有这四种德行的人,可称为士了吗?’齐湣王说:‘好啊!这正是我所谓的士了。’尹文说:‘大王如果得到这样的人,愿意任用他为臣子吗?’齐湣王说:‘那是我求之而不得的呀!’当时齐湣王正提倡勇武之风。于是尹文便说:‘假使这样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欺负而始终不敢抗争,大王还肯用他为臣吗?’齐湣王说:‘这还算什么士人?遭受欺侮而不敢抗争,多么耻辱!对于这种甘愿受辱的人,我是决不会用他为臣的。’尹文说‘虽然受到欺侮而没有抗争,可是并没有失去这四种德行呀!既然没有失去四种德行,那也就并没有失去作为士的资格!然而,大王一会儿想用他为臣,一会儿又不愿用他为臣。那么您刚才所说的“士”的标准,难道又不算是“士”了吗?’齐湣王哑口无言了。”“尹文接着说:‘现在有位君主,打算治理他的国家,人民有过错他便处罚,没有过错也要处罚;有功劳便奖赏,没有功劳也要奖赏。这样管理他的国家,却反而埋怨人民不好管理,对吗?’齐湣王说:‘不对!’尹文说:‘我私下观察下面的官吏对齐国的治理,就像这样!’齐湣王说:‘寡人治理国家,倘若象先生说的那样,人民即使没有管理好,我也不敢埋怨的。不过我想情况不至于如此!’尹文说:‘我那样说岂敢没有根据?大王的法令规定:“杀人的处死,伤人的人受刑”。人们中有威慑于大王法令的,受到欺侮而始终不敢抗争,这是维护与遵守大王的法令。然而大王却说:“受到欺侮而不敢抗争,这是一种耻辱。”大王说这种行为是耻辱的,因而取消了他作为臣子的任职资格,本来并没有过错而大王却认为有错,因而国家取消了他作官的资格,不用他为臣了。不任用为臣就是一种惩罚,这是没有罪过而被大王惩罚了!既然大王以不敢抗争为耻,必然以敢于抗争为荣;以敢于抗争为荣,就是对抗争行为的肯定。也就必然起用这种人为臣了。就是对他的奖赏。这种人毫无功劳而大王却大加奖赏。这样,大王所奖赏的,正是官吏所要诛罚的;君主所肯定的,却是法度所不容的。赏、罚、是、非,四个方面互相错乱,这种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的情况,即使有十倍于黄帝才能的人,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齐湣王无从应答。所以我认为您的话,是类似齐湣王的言论。您只知道非难‘白马非马’之说,却不懂得依据什么去反驳,这正像齐湣王那样,只知道喜好‘士’的名号,却不懂得明辨‘士’成其为一类人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