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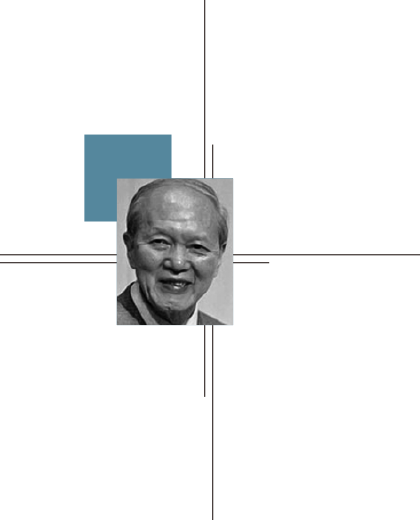
这是一所曾被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盛赞为“东方剑桥”的大学,它静静地矗立于西子湖畔,将学术之美与自然之美融为一体。1897年创办的浙江大学在抗战中无奈地成了一所“流亡大学”,师生们先后辗转于江西、广西等地,最后到达贵州。当时的竺可桢校长呈请教育部同意在沦陷区附近设立分校,教育部回电说可以在浙赣闵设立分校,于是,浙江大学在龙泉县坊下村设立了分校。分校在创办之初只有一年级,学生修完一年级的学分后就到学校总部继续读二年级。1943年秋天,谷超豪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在龙泉校区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学校位于龙泉城外十多里的一个小山村里,校舍设在坊下村一处旧时大户人家所建的大宅院里,这是一座四层的木结构楼房,摇摇欲坠,理学院、农学院和工学院都挤在一起,吃、住、上课都在里面。谷超豪所在的理学院一年级有二十几个同学,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里,白天上课还好说,只是夏天热一点,冬天冷一点而已。晚上自修就很惨了,这里偏僻,没有电灯,每个同学都在一个小破盘子里放上点桐油和几根灯草,大家都点起灯来,就像教室着火了一样,乌烟瘴气的,自修结束时每个人的鼻孔都是黑黑的。浙南气候湿润,夏天蚊虫成群,大家的业余生活全成了和蚊虫作战。吃的东西更差,每餐一小碗青菜,早餐喝稀饭,因为粮食少,每个同学的饭都是用秤称好分下来的。学生时代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点东西哪能吃饱呢,同学们个个都饥肠辘辘的,强忍着继续上课。

数学战略家谷超豪传吃住不好都还只是物质上的,让大家精神受折磨的则是村里居民们每晚没休没止拜佛求神的敲打声了。那时村里正流行鼠疫,大家听得多了,人心惶惶,因为身体都不好,都很担心染上这可怕的传染病。
不过,生活的艰苦没能吓倒这群热血青年。一年级的课程很多,有微积分(包括微分方程)、代数方程式论、立体解析几何、普通物理、英语、语文和中国通史,等等。数学要做大量习题,物理经常举行临时测验.谷超豪虽然一直没放下课业,但中学时期由于躲警报和教师生病,有的数学内容并没有教完,谷超豪这时就结合微积分,把中学的课程一并补上了。当时,大一的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直观能力、演算能力和解应用题的能力,为谷超豪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谷超豪原来有不太细致的毛病,通过学微积分也逐步克服了。他读了一本用综合方法写的射影几何著作,完全不用计算,便能把二次曲线的基本性质描述清楚,这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他也非常喜爱笛沙格(Desargues)定理、帕普斯(Pappus)定理和帕斯卡(Pascal)定理。通过这些学习,他慢慢对几何学有了偏爱。
虽然生活很艰苦、学业任务也不轻松,但青年人的幽默和乐观还是会不时地展现出来。谷超豪记得,那座大院的前方是块草场,大家利用课余时间把它辟为了操场,学生组织的歌咏队经常在这里举行活动,像《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黄河大合唱》等激情澎湃的歌曲经常从这里传遍整个村落。当时老师们住的是学校旁边一处简陋的木头房子,周围是看不到尽头的片片树林和点点茶山,十分荒凉。一到梅雨季节,这木头房子便外面下大雨,里面淅淅沥沥地下小雨。老师们无奈,只好把书本、被褥之类紧要的东西放在安全地带,然后找出锅碗瓢盆等放在漏水处接水,雨水滴滴答答地敲打着这些家什,竟像是森林的乐手在演奏。学生们听的次数多了,便给这木房子起了个很有诗意的名字——风雨龙吟楼,老师们听后觉得不错,很写意,这个名字便传开了。可见,当时浙大的师生都很有以苦为乐的达观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谷超豪回到杭州校区继续读书。总校老师的教学比分校老师更加严格,每门课都有习题课,助教们时常叫学生上黑板做题目,做不出的就站在那里思考,被大家戏称作“挂黑板”。当时,苏步青老师教“综合几何”,陈建功老师教“复变函数论”,谷超豪对这两门课都很感兴趣,他便挤出时间,两边的课都去听,几节课下来,便觉得自己以前学的东西很肤浅,和老师差距很大。他原来自以为数学功底不错,可以轻松获得两位大家的赏识,其实,自己要努力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啊!于是,谷超豪课上仔细听讲,课下认真自学,有不懂的问题就积极地请教老师,进步之大之快也就不言而喻了。
谷超豪记得,当时最难的课程是“数学研究”。这门课程要求学生自己翻阅藏书,读论文,然后把结构以做报告的形式展现出来,还要回答老师提出的各种相关问题。这门课不及格的同学不能毕业。苏步青和陈建功两位老师分别指导微分几何和函数论方面的专题讨论。因为课程难度大,所以学校规定每个学生只能参加其中之一。这需要在课下做大量的准备,还要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每个同学来说都是很费时、费力的。可是这一年,苏步青和陈建功共同商定,认为少数学生学习成绩优秀、能力强的,可以多压担子,破例允许谷超豪和另一名同学两个专题都可以参加。谷超豪得到消息后很开心,虽然他要做的事情更多了,但有机会聆听两位数学大师的教诲,他累并快乐着。
除了数学,物理也是谷超豪很感兴趣的一门课。当时,理论力学是学校开设的必修课,他花了很多力气,查阅参考书,做习题,课上每次都有不同的见解,深得教物理的周北屏教授的喜欢。到了三四年级,他又选修了物理系的量子力学、相对论、理论物理等课程。需要强调的是,对物理课程的广泛涉猎,直接为谷超豪后来在二十世纪70年代研究和规范场有关的数学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正是因为谷超豪的刻苦求知和上下求索的好学精神,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当了助教。1949年,杭州解放,谷超豪被调到中国科协杭州分会工作,担任分会秘书和党组书记。由于中国科协杭州分会在位于杭州长生路4号,谷超豪便把这一时期的工作戏称作“长生路4号精神”,这当然也是大家齐心协力让科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992年,为庆祝母校浙江大学95周年校庆,谷超豪作诗两首。
一首是:
寂寞山城
 夜,激情浙水边。
夜,激情浙水边。
学子愤国事,师母愁炊烟。
弦歌终不辍,江潮更无闲。
不畏古怪多,秧歌堪流连
 。
。
作品写的是,因为战事,浙大被迫迁到山城龙泉。师生们忧国忧民,对祖国满怀热情。没有粮食,苏步青的妻子,也就是谷超豪的师母为了吃饭发愁——没饭吃是当时龙泉最大的生活困境。但大家努力克服困难,终于迎来了解放的秧歌。
另一首是:
春风勤拂拭,秋实结满枝。
九五育才业,四十求是思。
湖山多艳丽,校园尽新姿。
百岁庆贺日,寰宇极目时。
谷超豪40年后回望母校,校园一片新景象,希望母校可以发扬光大,成为世界一流的学府。
1957年,谷超豪被派到莫斯科大学进修两年
说起莫斯科大学,首先映入眼帘的当属列宁山了。它高出河面约60米—70米。山色墨绿,水波瓦蓝,山青水秀,景色迷人。没有到过这儿的人,对它无限向往;来到这儿的人,往往流连忘返;而离去的人,心中则充满了深情的怀念和甜蜜的回忆。苏联解体后,列宁山又恢复了它1935年前的旧名——沃罗比约夫山,意即“麻雀山”。沧海桑田,物换星移,但矗立此山之颠的莫斯科大学主楼顶端那光彩夺目的五角红星,却一直熠熠生辉。

从1957年9月开始,谷超豪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度过了两个学年。当时,谷超豪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副教授,是作为进修教师去莫斯科从事研究工作的。此前,1952年的时候,苏步青、陈建功等浙江大学的数学精英,响应全国高校院系的大调整,来到了复旦大学,正在北京“俄专”学习俄语的谷超豪闻讯也来到了复旦,与导师会合。院系调整之前,复旦大学没有数学系,院系调整中,浙江大学数学系、复旦大学数学系和同济大学等一些数学家们组成了复旦大学数学系,而在浙大已经成为讲师的谷超豪则一方面给化学系开设高等数学,另一方面给陈传璋做助手,辅导高级微积分。随着各位老师的默契配合和费心钻研,复旦大学数学系很快就成了全国高校最有实力的数学系之一了。在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针对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俱兴的局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着手制订国家科学发展规划,陈建功和苏步青应邀参加,随后,毛主席对苏步青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回来后,苏、陈两位先生按照国家的学科发展理念把眼光从本学科专业延伸到了整个数学学科的发展,为了配合新学科的扩展,苏步青和陈建功向复旦大学党委建议,让谷超豪去莫斯科大学进修两年,希望他可以将自己的数学研究扩展到更新更广阔的领域中去。
谷超豪一到莫斯科,就被那里的学术环境所吸引。他原来学的是微分几何,而莫斯科大学就有两个研究性的微分几何讨论班,其领导人分别是菲尼柯夫教授和拉舍夫斯基教授,两个班谷超豪都参加了。讨论班每周定期举行讨论,从不间断。参加者不仅有莫斯科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还有其他大学的有关教师。师生共聚一堂,确是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他们研讨学术十分严肃认真,相处又非常融洽。这样的讨论班,就数学的各个分科而言,就有二三十个。第二年,谷超豪还参加了以莫斯科大学校长彼得罗夫斯基院士为首的偏微分方程讨论班。谷超豪觉得,这些讨论班总是以报告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主,从而保证了研究方向的稳定性,促进了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使研究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这种讨论班也反映出他们艰苦治学的精神——白天要保证学生上课,讨论班就只能安排在晚上。例如,菲尼柯夫教授领导的讨论班总是安排在星期六晚上,三个层次的报告往往从下午6时一直持续进行到晚上10时,连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了。
莫斯科大学学术环境的另一特点是有许多高水平的专门课程。谷超豪到那里的第一个学期就选读了盖里芬特通讯院士和奥列尼克教授的两门课程,都是关于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间断解的,反映了当时的最新成就和重要的研究方向。后来,他又去听了拉舍夫斯基教授关于场论的课程。由于力学和数学关系紧密,他也选听了一些流体力学的课程。这些课程,对于谷超豪后来的研究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另一方面,莫斯科大学和其他国家的数学界也有一定的交流。莫斯科数学学会每星期四晚上都在莫斯科大学举行学术报告会,常有国外著名学者来作报告。例如,谷超豪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法国著名数学家勒莱院士。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法国几何学权威E·嘉当院士从30年代到40年代三次应邀去苏联讲学,对苏联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谷超豪去苏联之前,他的老师苏步青教授对他说,E·嘉当的许多工作都被后人充分发展了,但他关于无限变换拟群的理论,由于难度大,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谷超豪听过苏步青以E·嘉当所著的《黎曼几何》为教材的课程,在选择无限变换拟群的课程后,又精读了一遍那本书,并对E·嘉当的其他著作一一进行研读。谷超豪发现自己在莫斯科大学的确具备了研究这个课题的良好条件,于是他每隔两三周就对有关的问题作一次报告。在一年时间里,他就写出了好几篇论文。后来的总结成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E·嘉当变换拟群的通性及其对微分几何的应用》,并于1959年7月通过答辩,且跳过副博士阶段,破例被直接授予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
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同事们对中国学者是非常友好的。拉舍夫斯基、菲尼柯夫等教授时常邀请谷超豪到他们家里做客。他取得学位后,他们还为谷超豪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给他非常热情的祝贺。1959年,在他和许多中国同志回国前夕,校长彼得罗夫斯基院士亲自为他们送行,并向他道贺。教研室的秘书对谷超豪的生活安排、研究计划、发表文章、会见其他学者等等,也都给予了全方位的关心。这一切,给谷超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今,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以上提到的教授,有几位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谷超豪还深深地怀念着他们。与此同时,他也为苏联学者以辛勤的劳动在本国土地上建立起像莫斯科大学那样强大的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感到非常的钦佩。
回国后,谷超豪为复旦大学力学专业的高年级同学开设了空气动力学、差分方程稳定性等课程,同时,他还在数学系成立了专门小组,研究流体力学中的偏微分方程问题。谷超豪主要负责研究双曲型方程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他率先解决了一批高维空间的混合型方程的边值问题、化混合型方程为对称方程组的问题以及高阶混合型方程的一类边值,并对《岩波数学百科全书》中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他的研究是结合国家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所描绘的蓝图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的,比如,大家熟知的“两弹一星”是当时国家的重点攻关项目,就是因为谷超豪最先给出了机翼超音速绕流问题的数学证明,使这项研究成果比西方早了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