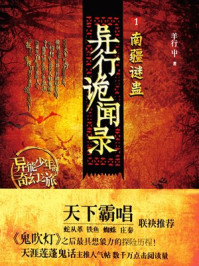玻璃门上,一张招贴宣布: 钢琴家瓦尔多·布伦特每天十八时至二十一时在希尔顿饭店酒吧间演奏 。
酒吧间客满,没有座位,只在一位戴金边眼镜的日本人的桌边还有一把空的扶手椅。我俯下身问他是否可以坐下,他没听懂,等我坐了下来,他丝毫不予理会。
一些美国或日本顾客走进来,他们互相打招呼,说话声音越来越响。他们停留在桌子之间,有些人一杯在手,靠着椅背或扶手。一位年轻女子甚至高高坐在一位灰头发男人的膝盖上。
瓦尔多·布伦特迟到了一刻钟,他坐到钢琴前。一个胖胖的小个子男人,秃脑门,唇髭稀疏。身穿一套灰西装。他先掉过头来,环视坐得很挤的一张张桌子。然后用右手轻抚琴键,随意地用力弹了几个和弦。我很幸运,坐在离他最近的一张桌边。
他开始弹奏一个曲子,我想是《在老巴黎的堤岸上》。但是谈话声和笑声使人几乎听不见音乐,我虽然离钢琴很近,也捕捉不到全部的音符。他镇定自若地继续弹奏,上身笔直,头向前倾。我为他感到难过:我想在他一生的某个时期,曾有人聆听他弹钢琴。后来他不得已,渐渐习惯了盖住他琴声的嗡嗡响个不停的嘈杂声。如果我讲出盖·奥尔洛夫的名字,他会说什么呢?这个名字会使他暂时放弃继续弹奏乐曲的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吗?抑或它不再唤起他的任何回忆,正如琴声压不住交谈的喧哗?
酒吧间渐渐空了,只剩下我、戴金边眼镜的日本人和原先坐在灰头发男人膝上的年轻女子。现在她坐在酒吧间尽里面一位身穿浅蓝色西服的红脸胖子身边,讲德语,声音很大。瓦尔多·布伦特正演奏一支我十分熟悉的徐缓的曲子。
他朝我们转过身来。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愿不愿意我弹些特别的曲子?”他问道,嗓音冷冷的,露出轻微的美国口音。
我身边的日本人没有反应。他纹丝不动,面部很光滑,我担心一阵过堂风会把他从椅子上刮倒在地,因为他真像一具用防腐香料保存的尸体。
“请弹《萨格·瓦罗姆》吧。”尽里面的女子用沙哑的喉咙喊道。酒吧间的灯光暗下来,在有些舞厅,一支慢狐步舞曲的旋律一响,灯光就会变暗。他们借机互相搂搂抱抱,女人的手伸进红脸胖子衬衣的领口,再继续往下伸。日本人的金边眼镜闪着短促的微光。布伦特坐在钢琴前,活像个跳动的机器人:《萨格·瓦罗姆》的曲调要求不停地用力在键盘上奏出和弦。
正当他身后有个红脸胖子抚摸着一位金发女子的大腿,一具日本木乃伊在希尔顿酒吧间的一把扶手椅里坐了好几天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什么也不想,我敢肯定。他迷迷糊糊的,愈来愈麻木。我有没有权利使他突然摆脱麻木,唤醒他心中某个痛苦的回忆呢?
红脸胖子和金发女子离开了酒吧间。他们一定去开房间了。男人拉着她的胳臂,她险些绊倒。只剩下我和日本人了。
布伦特又朝我们转过身来,冷冷地说:
“你们要我弹别的曲子吗?”
日本人连眉头也没皱一下。
“先生,请弹《爱的余韵》吧。”我对他说。
他弹起这首曲子,节奏慢得出奇,旋律似乎松垮下来,陷入了沼泽地,音符难以挣脱出来。他有时停止弹奏,仿佛是个筋疲力尽、步履蹒跚的行路人。他看了一下表,蓦地站起来,朝我们点了点头:
“先生们,现在二十一点了。晚安。”
他出去了。我紧随其后,把那具日本木乃伊留在酒吧间的死尸埋葬地。
他穿过走廊,走到空无一人的门厅。
我追上了他。
“是瓦尔多·布伦特先生吗?……我想和你谈谈。”
“谈什么?”
他朝我投来被追捕者的目光。
“谈你认识的一个人……一位叫盖的女子。盖·奥尔洛夫……”
他呆在门厅中间一动不动。
“盖……”
他瞪大眼睛,仿佛探照灯的灯光对准了他的脸。
“你……你认识……盖?”
“不。”
我们走出了饭店。一长列男女在等出租车,他们身着颜色刺目的晚礼服:绿色或天蓝色缎子长连衣裙,石榴红无尾长礼服。
“我不想打扰你……”
“你并不打扰我,”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听人谈起盖了……可你是谁呀?”
“她的一个表亲。我……我想知道有关她的细节……”
“细节?”
他用食指揉着太阳穴。
“你想要我对你谈什么呢?”
我们走上沿着饭店一直通向塞纳河的一条窄街。
“我得回家了。”他对我说。
“我陪你回去。”
“那么,你真是盖的一个表亲?”
“是的。我们家的人想知道她的情况。”
“她早已死了。”
“我知道。”
他疾步而行,我几乎跟不上他。我努力和他齐头并进。我们走到了布朗利码头。
“我住在对面。”他指着塞纳河对岸说。
我们踏上了比拉凯姆桥。
“我无法告诉你许多情况,”他对我说,“我是很久以前认识盖的。”
他放慢了脚步,仿佛他感到自己的处境是安全的。他刚才走得那么快,或许是因为他以为有人盯梢,抑或为了甩掉我。
“我原先不知道盖还有亲人。”他对我说。
“有……有……乔吉亚泽那方面……”
“对不起?”
“乔吉亚泽家……她的外祖父名叫乔吉亚泽……”
“噢……”
他停下脚步,依在桥的石栏杆上。我不能照样做,因为这样我会头晕。于是我面对他站着。他迟疑了一下才开口。
“你知道……我和她结过婚?”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旧的文件上有记载。”
“我们一道去纽约的一家夜总会……我弹钢琴……她要我和她结婚,仅仅因为她想留在美国,不愿移民局找她麻烦……”
回想起这件事,他摇了摇头。
“这是个古怪的姑娘。后来,她与吕基·吕西亚诺交往……这人是她到 棕榈岛 娱乐场工作时认识的……”
“吕西亚诺?”
“对,对,吕西亚诺……他在阿肯色州被捕时,她正和他在一起……后来,她遇到一位法国人,我听说她和他一道去了法国……”
他两眼有了神,冲我微笑着。
“先生,我很高兴能够谈谈盖……”
一辆地铁从我们头顶上驶向塞纳河右岸。接着又有一辆驶往相反的方向。轰隆轰隆的响声盖住了布伦特的声音。他同我说话,我只看到他的嘴唇在动。
“……我所认识的最漂亮的姑娘……”
我好不容易才听清的这半句话使我大为泄气。夜里,我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呆在桥中间,试图从他口中得到关于我本人的一些细节,而地铁的隆隆声使我听不见他的话。
“我们往前走走好吗?”
他那样全神贯注,没有回答我的问话。他恐怕有很长时间没有想到这位盖·奥尔洛夫了。关于她的回忆一股脑儿浮出了水面,如一阵海风把他吹得晕头转向。他靠着桥栏杆,没有动。
“你真的不想再往前走走吗?”
“你认识盖吗?你遇见过她?”
“没有。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得到一些细节。”
“这是一位金发女子……绿眼睛……金黄头发……很特别……怎么说呢?一位……灰黄头发的女子……”
一位灰黄头发的女子。她也许在我的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我必须仔细看看她的相片。渐渐地,一切都会回想起来的,倘若他最终不能给我提供更确切的线索。找到了他,找到了这位瓦尔多·布伦特已算幸运了。
我挽起了他的胳臂,因为我们不能在桥上停留。我们沿着帕西滨河路走着。
“你在法国又见到她了吗?”我问他。
“没有。我到法国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她自杀了……”
“为什么?”
“她常常对我说她怕衰老……”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与吕西亚诺的事了结后,她遇到了那位法国人。那段时间我们见过几次面……”
“你认识他吗,那个法国人?”
“不认识。她告诉我她即将和他结婚,以便取得法国国籍……有个国籍是她摆脱不掉的念头……”
“可是你们离婚了?”
“当然……我们的婚姻维持了六个月……恰好可以平息移民局企图把她驱逐出美国的风波……”
我必须聚精会神才能把她的身世连贯起来,尤其因为他的嗓音十分低沉。
“她动身去了法国……我再也没见过她……直至我听说……她自杀了……”
“你怎么知道的?”
“通过一位美国朋友,他认识盖,当时正好在巴黎。他寄给我一小张剪报……”
“你留着吗?”
“留着。它一定在我家里,一只抽屉里。”
我们来到了特罗卡德罗花园。喷泉被灯光照得雪亮,路上有许多车辆和行人。喷泉前和依埃纳桥头有成群的旅游者。虽是十月一个星期六的夜晚,但是秋风和煦,漫步者众多,树木尚未落叶,倒像是春天一个周末的夜晚。
“我的家在那边……”
我们走过花园,来到纽约大街。在河堤的树下,我有一种做梦似的不愉快的感觉。我已经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如今只是一个在周末夜晚的和暖空气中游荡的鬼魂。为何要再结已断的纽带,寻觅早已砌死的通道?这个在我身边走着,蓄唇髭、胖胖的小个子男人,让我难以相信这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真滑稽,我突然想起来盖在美国认识的那个法国人的姓名了……”
“他叫什么?”我问道,声音直抖。
“霍华德……这是他的姓氏……不是名字……等等……霍华德·德……”
我停住脚步,朝他俯下身去。
“霍华德·德……?”
“德……德……德·吕兹。吕……兹……霍华德·德·吕兹……霍华德·德·吕兹……这个姓氏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半英语……半法语……或者西班牙语……”
“名字呢?”
“这个……”
他做了个无能为力的手势。
“你不知道他的长相吗?”
“不知道。”
我要把盖和老乔吉亚泽以及我认为是自己的那个人合照的相片拿给他看。
“他从事什么职业,那位霍华德·德·吕兹?”
“盖告诉我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他什么也不干。”
他轻声笑了。
“不……不……等等……我想起来了……他在好莱坞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在那儿,盖告诉过我他是演员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
“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
“对……在吉尔伯特的晚年……”
汽车在纽约大街上疾驰,但人们听不到发动机声,这增强了我的梦幻感。它们倏忽而过,声音沉闷,流畅,仿佛在水上滑行。我们来到阿尔马桥前面的步行桥。霍华德·德·吕兹。有可能这是我的姓氏。霍华德·德·吕兹。对,这几个音节唤醒了我心中的某样东西,某样和照在物体上的目光一样稍纵即逝的东西。如果我是这个霍华德·德·吕兹,我在生活中一定有些古怪,因为在那么多一个比一个体面和吸引人的职业中,我竟选择了当 约翰·吉尔伯特心腹 的职业。
正要走到现代艺术博物馆时,我们拐进了一条小街。
“我住在这儿。”他对我说。
电梯的灯坏了,电梯刚往上升,楼道的定时灯便灭了。黑暗中,我们听到了笑声和音乐声。
电梯停下,我感到身边的布伦特在找楼梯口的门把手。他打开了门,我走出电梯时撞了他一下,因为周围漆黑一片。笑声和音乐声来自我们所在的楼层。布伦特用钥匙开了门。
我们走进去,布伦特让门半开着。我们站在门厅中间,吊在天花板上的一只无罩灯泡光线很弱。布伦特呆在那儿发愣,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辞。音乐震耳欲聋。从套房里走出一位红棕色头发、身穿红浴衣的少妇。她用吃惊的眼神打量着我们两个。宽松的浴衣露出了一对乳房。
“我妻子。”布伦特对我说。
她朝我微微点了点头,用两手把浴衣的领子拉到脖颈。
“我不知道你回来这么早。”她说。
我们三个一动不动地呆在灯光下,它把我们的脸照得发白。我朝布伦特转过身去。
“你应该事先给我打个招呼。”他对她说。
“我原先不知道……”
一个谎言被当场拆穿的孩子。她垂下了头。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停止了,响起了萨克斯管的优美旋律,它那样纯净,仿佛被空气稀释了。
“你们人很多吗?”布伦特问道。
“不,不……几个朋友……”
从微启的门缝中露出一张脸,一位金发女子的脸,头发剪得很短,涂着浅色的,几乎是粉红色的口红。接着又露出一张脸,一位皮色晦暗的褐发男子的脸。灯光下,这些脸好似假面具,褐发男子微笑着。
“我得和朋友们回去了……过两三小时再回来吧……”
“很好。”布伦特说。
她跟在另外两个人后面离开了门厅,然后关上了门。传来了笑声和互相追逐的声音。接着,又响起震耳欲聋的音乐。
“来!”布伦特对我说。
我们又回到楼梯。布伦特揿亮了定时灯,在楼梯上坐下。他示意我坐在他身边。
“我妻子比我年轻许多……相差三十岁……绝不该娶一个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女人……绝不该……”
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头。
“这绝不会成功……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你记住这个,老弟……”
定时灯灭了。看来布伦特根本不想再开灯。我也一样。
“如果盖看到我……”
想到此,他放声大笑。古怪的笑声,在黑暗中。
“她不会认出我……我至少重了三十公斤,自从……”
又一阵大笑,但和上一次不同,更神经质,更勉强。
“她会非常失望……你明白吗?钢琴家在饭店的酒吧间……”
“但她为什么失望呢?”
“而且再过一个月,我会失业……”
他紧握我的手臂,在二头肌部位。
“盖以为我将成为另一个科尔·波特……”
蓦地,响起女人的叫声。它来自布伦特的套房。
“出什么事了?”我问他。
“没什么,他们在寻开心。”
一个男人的嗓子吼道:“你给不给我开门?达妮,给不给我开门?”
一阵笑声。门喀喀作响。
“达妮是我妻子。”布伦特悄声对我说。
他站起来,打开定时灯。
“咱们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我们穿过现代艺术博物馆前面的广场,在台阶上坐了下来。我看见稍低处车辆在纽约大街上穿梭,这是仍有生命的唯一征兆。我们周围一片死寂,连塞纳河彼岸的埃菲尔铁塔,平常如此令人心安的埃菲尔铁塔,也好似一堆经过煅烧的废铁。
“这里呼吸顺畅。”布伦特说。
的确,一阵和煦的风吹过广场,吹过形成一个个黑影的塑像和尽里面的大圆柱。
“我想给你看几张照片。”我对布伦特说。
我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我打开它,从里面抽出两张照片:盖·奥尔洛夫和老乔吉亚泽以及我以为是自己的那个人合照的那张,还有她小时照的那张。我递给他第一张照片。
“这里什么也看不见。”布伦特喃喃地说。
他按了一下打火机,风把火苗吹灭了,他不得不按了好几次。他用手心遮住火苗,把打火机凑到照片上。
“你看见照片上有个男人吗?”我对他说,“在左边……尽左边……”
“看见了。”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他俯身在照片上,手搭凉棚保护打火机的火苗。
“你不觉得他像我吗?”
“我不知道。”
他又把照片细看了一会儿,然后还给了我。
“盖完全是我认识她时的模样。”他声调悲凉地说。
“喏,这是她小时候的相片。”
我递给他另一张相片,他就着打火机的火苗细细端详,依然手搭凉棚,活像正在做一件极精密的活儿的钟表匠。
“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他对我说,“你还有她的相片吗?”
“没有,很可惜……你呢?”
“我原先有一张结婚照,可是在美国丢失了……我甚至怀疑她自杀时我是否保留了那张剪报……”
他的美国口音,起先不易察觉,现在愈来愈重了。因为疲倦?
“你经常这样等着回家吗?”
“越来越经常了。可开始时很美满……我的妻子十分可爱……”
因为有风,他好不容易才点燃香烟。
“盖看到我这种处境会大吃一惊……”
他走近我,一只手搭在我的肩头。
“老弟,你不觉得她死得正是时候吗?”
我注视着他。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圆的。脸庞,蓝眼睛,甚至修剪成圆弧状的小胡子。还有嘴巴,胖乎乎的手。他使我联想到孩子们用线牵着的气球,他们有时松开手,看看气球能飞多高。他的姓名瓦尔多·布伦特鼓胀着,好似一只气球。
“老弟,很抱歉……我没能告诉你许多关于盖的事情……”
我感到由于疲惫和沮丧,他的身体变得沉重了。但我留神守护着他,因为我担心广场上一刮风他会飞起来,留下我一个人和我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