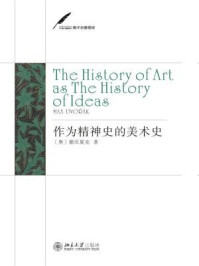我们说“荷马史诗”反映了古希腊“英雄时代”的社会氛围,那么,在“英雄时代”前后又是什么样的时代?古希腊人是如何认识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历史的呢?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古往今来的历史哲学家所共同关心的,因为历史观念的形成,便以此为核心。而思想家、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进程所作的反思,是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
古希腊人不仅以他们对自然界的好奇而著称,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奥秘也颇具探究之心。率先的一位便是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的赫西奥德(Hesiodos,约公元前700年)。在他的《神谱》(Theology)中,赫西奥德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是“黄金时代”,那时的人们无忧无虑,过着神仙般的生活;接下来是“白银时代”,出现了残忍的行为和对战争的欲求;“紫铜时代”的人们命运更为悲惨,无休止的战争使他们同归于尽;接着的“英雄时代”,此时战争继续连绵不断——“荷马史诗”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起——最后那些半神半人的英雄都为战火所吞噬。赫西奥德把他自身的时代称为“黑铁时代”,这时,虽然轰轰烈烈的战争已不多见,但人们的生活仍然被凄苦、邪恶和死亡所缠绕,失去了往日的英雄气概,跌入了庸碌而平淡的生活环境之中。在他的诗篇《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中,赫西奥德更进一步描述了“黑铁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中他本人亦粉墨登场,但遭遇却十分悲惨,为他的兄弟所欺。面对非正义的行为,赫西奥德求助于神意的干涉,既表现了时代的险恶,又突出了神对人类的最终主宰。
赫西奥德的历史构想毫无疑问是颇为机械的,具有一种命定论的倾向。这种悲观和退化的历史观,在当时有着深远的影响,称得上是古希腊历史观的代表。
一、循环中的升与降
古希腊人是一个富于思想的民族。他们对自然、人生的探究在许多地方启发并造就了西方的文明。希腊许多思想家的著作至今仍被引为经典。然而,面对历史的思考,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这些赫赫有名的哲学家则与诗人赫西奥德并无太大不同;他们承袭了历史退化的观念,并以循环论相辅,勾勒历史的演变。这里仅以柏拉图的论述为例。
在《法律篇》(Laws)中,柏拉图断言:上帝创造了世界,因此,宇宙之始必然是颇为完善的。但可惜好景不长,因为里面竟然有着衰败的种子。大约过了36000年,世界便开始呈现衰落的朕兆,并且逐步退化。这主要是因为上帝逐渐放松了对他的管辖,因此他手创的秩序便遭到了破坏。最后,世界陷入了大混乱之中。这时,上帝又重新掌起了舵,一切美景便又重新开始。由此柏拉图指出,人类历史的前36000年是所谓的“黄金时代”。在《克利提乌篇》(Critias)中,柏拉图更明确地指出理想的社会是在雅典(Athens)的改革家梭伦(Solon)之前9000年。
柏拉图还以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例来证明他的历史演化理论。他认为,在人类退化之初,产生了贵族政治,接着便每况愈下,依次产生了荣誉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政治制度退化的原因,在于人种本身的退化,而人种的退化,又是由于国家对婚姻管理的松弛和错误所造成的。
与赫西奥德相比,柏拉图的历史论述显然要充实得多,但其核心则并无二致,都带有悲观主义的倾向。而且柏拉图用各种政体的递嬗来说明社会的退化,也有片面的地方,与后人的理解颇为不同,特别是对民主制的看法上。事实上,要比较政体的孰优孰劣,本非易事,不免见仁见智。以此来阐说历史的演化,让人有捉襟见肘之感。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的《法律篇》,为哲学家晚年的作品。阅历的增长使得人们对历史的变迁有着深入的体会,并产生念旧的心情。我们可以了解到,柏拉图晚年的心境,已经与他写作《理想国》(Republics)时不太相同了。他已经失去了那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对社会的动荡,似乎也有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
柏拉图之后,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为详细地考察了政治体制的问题,写成了《政治学》(Politics)一书。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历史进程提出明确的看法。他只是强调学术、科学和政体都是重复出现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也倾向于认为历史循环演化。
历史循环的观念在希腊社会十分流行,一直影响到古典时代后期的斯多噶(Stoics)派的哲学家。他们尊奉这一信条,并据此对世界的发展作了周期的划分,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衰亡,甚至坠入深渊,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不过,这一循环论的历史观念,只是希腊时代斯多噶派所持的理论,到了后来则有所不同。但就总体而言,身处希腊化时代的斯多噶派哲学家对历史和现实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他们目睹古典时代的衰落,古典文化的式微,无可奈何,听之任之,主张与世无争,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这与希腊人在早年向外殖民时代的进取精神大相径庭。斯多噶派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一种灾变说,即认为宇宙在经过数个阶段的发展之后,会有一场大灾难降临,一切于是又得重新开始。
以上所述的主要是希腊哲学家的历史观。古希腊的史学家尽管很少直接阐述他们对历史演化的看法,但我们从他们写作历史的意向中还是能发现他们的历史观。如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赫克特斯(Hecateus,约公元前540—前476年)便有一雄图大志,想把古代希腊人的历史与神话传说联系起来,写出一部一线相传的希腊史,几有“通古今之变”之概。可惜他的著作已大部分散佚,未能流传下来。后人只能在断编残简中觉察到他的意向,而无法考察他的成就。但既然有此大志,我们可以推想赫克特斯或许已经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也有历史的时间概念,比纯粹的循环论,有高明之处。
希罗多德在西方被誉为“史学之父”(西塞罗语)。他的《历史》(Histories),以其宽广的视野、丰厚的史实记载和求真的精神,赢得了后人的称赞。但是,希罗多德似乎并不善于对历史作出总体的概括:他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常常迷失于众多的奇闻逸事的叙述之中。不过,在《历史》的起始,希罗多德表达了他写作该书,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录下来”。这说明,在希罗多德的眼里,过去的业绩对后人有启示的作用,即历史能不断延续。在这一不断演化的过程中,有些历史事件能获得永恒的特质,进而超越时空的限制,不断重现。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观,希罗多德经常将发生于不同时代的事件作类比。这显然不符合现代历史学的要求,但却能反映希罗多德对历史的认识,体现了他记述历史的特点。Donald Kelley因为认为希罗多德的史学是古希腊史学的一种类型,与以后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年)的史学成对比。前者追求广博,寻找人类的共同特征,而后者则注重当代的事件,研究和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在史料的审定、史实的记述和写作的结构等方面都比希罗多德高出一畴。他们尽管处于同一时代,但从历史学的发展来衡量却恍如隔世。修昔底德并且有明确的历史观,在书的开首,修昔底德便阐明了他对历史方法和目的的看法。他指出:
虽然对于远古时代,甚至对于我们当代以前的历史,由于时间的遥远,我不能完全明确地知道了。但是尽我的能力所及,回忆过去,所有的证据使我得到一个结论:过去的时代,无论在战争方面,或者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
隔了几段,他又说道:
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久远的。从他所看到并且曾参与的战争出发,修昔底德断言他那个时代是希腊历史发展的高峰;而从人性不变的思想出发,他又认定历史是循环发展的。历史著作的重要性就在于给后来者提供殷鉴,免蹈覆辙。这些认识,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能依稀见到,但修昔底德表达得明确得多。这种历史观既承认历史的循环发展,又指出各个阶段的优劣,与希腊哲学家的观点相一致,称得上是古希腊时代通行的历史观念。
历史循环论通常将过去与现在相等同,看不到历史在时间上的变化。这在古代世界并不是罕见的现象,非古希腊所独有。我国古代追慕三代的古风,甚至言必称尧舜,认为遥远的古代能成为现代的楷模,就是这样的例证。这种思想在古代产生,有着多种原因,但本质上都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抗争中的某种失败和消极的心理,以求某种精神寄托。这一寄托可以指向天国,将希望放在遥远的天庭,也可以放在人世,但通常是在已经过去的时代。
就古希腊社会来说,历史循环论的盛行还有其独特的原因。众所周知,古希腊的鼎盛时代是以城邦制度的繁荣为特征的。这一制度对于希腊文化的发展自然有其贡献,但城邦之间连绵不绝的争战,让人无法产生希腊社会统一整体的意识。同时,城邦制度所带来的变动无常、须臾生死的生活,也使得希腊人热衷于探究恒常的、永久的本体或本原,而没能对逐渐消逝、流动不居的历史作出深沉的思索。这便造成了希腊历史思想的简单化。而构成历史循环论核心的灾变思想,实际上也是当时希腊世界战乱频仍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
二、什么是史学?
英国史学家John Bury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们(指希腊人)不是最早用编年形式记录人类活动的人,然而却是最早采用批判方法的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开创了历史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才成为西方史学的最早模式,虽然他们与其前辈和同代人一样,缺乏严格、精确的时间观念。
这样,人们便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个问题:历史学和神学、传说、史诗等究竟区别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现在看来,一定有许多种,但并不都适用于分析古希腊史学的诞生。因为西方史学的初始形式毕竟太粗糙、原始了。但是有一条区别还是明显的,即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乃至赫克特斯的著作中,普遍存在着求真的精神、写实的态度和分析的眼光。正是这些因素使他们逐步摒弃了虚构和想象,获得了历史学家的称号。
希腊历史学家正是在这样一种探究、写实的精神氛围中产生的。在古希腊文中,“ιστορια”(Historia,历史)一词的原意是“对真相的探求”,含义相当广泛,并不特指历史。相反,“logoi”(记事)一词接近于历史的含义。以后,经过爱奥尼亚地区的“说书家”(logographoi,storytellers)的努力,特别是他们对事实真相的探求精神,人们就逐渐把两个词合二为一,把他们的著作称为“历史”了。
对于历史真相的追求,从赫克特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希腊化时代的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0—前118年)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里面蕴藏着一种不断深化的历史认识。赫克特斯在《谱系志》(Genealogies)中开宗明义:
米利都人赫克特斯谨此申言: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关于希腊人的传说纷纭复杂、各异其趣,但据我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这是求真精神的最早记录。“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曾经多次提及他的历史方法。因为他希望让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保存下来,他便尽可能地搜集遗闻旧事,几乎有闻必录,甚至把那些他个人也觉得“不可索解”的事情也照样收录。不过,希罗多德还是深知历史真实性的重要。他一再告诫读者:
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他自己虽然缺乏鉴别史料的能力,但仍然有着追求历史真相的愿望。而且,他在写作中也常常从当时存在的各种不同说法中作了明智的选择。他对那些认为不可信的东西也同样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因此,希罗多德固然在分析、批判史料方面还不够大胆、果断,这是他未能彻底摆脱“说书家”影响的表现,但从治史的诚信态度来看,希罗多德还是无愧于“史学之父”这一桂冠的。正如Donald Kelley指出的那样:
尽管希罗多德的方法粗糙,既像游记又像口头传闻,但他绝对不是不加批判的。譬如他区别了事实和神话,他知道耳闻和目睹的分别,他也知道事件发生的原因(aitia)与前奏(prophasis)。如果说希罗多德治史尚有不足之处,那么修昔底德则似乎要先进得多,尽管他只比希罗多德晚生二十多年。无论在理解历史、分析史实或者批判史料、写作风格等方面,修昔底德仿佛都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无怪乎休谟(David Hume)会说,修昔底德的著作是西方历史学的真正开端。
修昔底德有一段名言: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这里所体现的已经不是一种主观上的求真精神或愿望,而是的确付诸实践的。希罗多德只是在书中提醒读者要辨别真伪,而修昔底德则亲自检验事实,力争把考核过的、可信的事实告诉读者,有着近代历史学家的雄心。
修昔底德的治史方法给希腊人留下了较深的影响。他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受到后人的推崇,续书者不少。尽管这些续写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们的作品也不能与原书相媲美,但由于修昔底德的影响,这些续书者都具有求真的精神和对史料的批判态度。因此,如果说批判方法的采用是西方历史学诞生的基石,那么修昔底德是一位奠基人。
到了古希腊晚期,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日益动荡,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阻抑,而罗马的兴起,又加速了希腊本土文化的“迁徙”。在罗马统治地中海的时期,希腊史学名家波里比阿进一步发展了修昔底德的求真作风。他说道:
真实对于历史,就像人的眼睛那样重要。人没有眼睛变成为终身残废,而历史缺乏真实,则成了无稽之谈。
波里比阿以其史书的翔实性赢得“历史学家中的史学家”的美誉。
从古希腊史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找到如何解答“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的线索。在西方,历史学的成长是随着对事实的追求而逐步诞生的。正是在对历史真相的不断探究和追索中,历史学的羽翼才逐渐丰满起来。可贵的是,古希腊的史学家与西方近代的史学家一样相信,真实的历史记载,即历史事件本身并不比虚构的文学作品逊色;他们力求记录希腊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惨烈和悲壮,也想描绘帕提侬神庙(Parthenon)和雅典娜神像的宏伟和精致。他们的努力,开始了历史学在西方的漫长发展历程。
三、从神到人
如果说“荷马史诗”是神、人共同活动的记录,那么,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则主要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将神话与历史作分别,应当也是历史学的根基之一。
如上所述,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他的《历史》尽管在现在看来,在内容上不免有些琐碎,但的的确确以人的活动为主题。《历史》一书共有9卷,其中第1卷至第5卷概述波斯帝国的兴起和扩张,记载了小亚细亚、埃及、西亚等地的风习和民俗,从第5卷第27节开始,专门叙述了希腊和波斯的战争,最后以希腊人在布拉达亚(Plataea)之战和密卡尔(Mycale)之战中的胜利作为结束。希罗多德偶尔也谈到神对人间事物的干预,但就总体而言,他已经摆脱了神主宰人世的观念,而是把着眼点放到了人的丰功伟绩上面。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曾经借人之口说道:
希腊的国土一直是贫穷的,但由于智慧和有效的法律,希腊人却得到了勇气;而希腊便利用了这个勇气,驱除了贫困和暴政。很明显,希罗多德在价值倾向上是偏向于希腊人的。但有意义的是,他的偏向集中于对人的智慧、人的力量的尊重和赞美。通观《历史》全书,人们很容易获得这样的印象:希罗多德有意无意地把赞颂希腊人的成就作为他的“任务”。他依次叙述了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从远古时代起的历次冲突,直到冲突的最高峰——希波战争。在这样一幅历史长景中来表现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的英勇和崇高,突出了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他们进行战争的正义性和希腊文化优越于波斯文化的方面。希罗多德对希腊人、雅典人的讴歌,与他的政治倾向颇有联系。很明显,他赞赏民主制,谴责君主制。他认为,正是因为雅典人能享受到平等和自由,他们才变得强大起来,从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人的活动和人的智慧固然是希罗多德《历史》的主题,他在历史活动的解释上还是表现出较浓厚的宿命论思想;《历史》一书有着不少神怪、迷信的描写。希罗多德在讲述人的苦难时常用“命中注定”这样的套语,以此来替代对历史现象原因的解释。一旦发生重大历史事变,希罗多德总相信会有神的启示:“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他相信奇迹、预言、幻象、梦兆、牺牲的占卜等都会有神启隐藏其中,而地震、星象怪异更是“上天垂示的朕兆”。在《历史》全书中,希罗多德提到朕兆的地方多达35次。这些都说明希罗多德对神具有一种虔信的感情。他也相信所谓的“神嫉说”,即如果人们过分要求幸福和财宝,便会受到神的惩罚。
然而,通过朕兆来描绘神对人事的作用,毕竟与“荷马史诗”中诸神的直接干预大不相同了。这说明,神在人的历史中已经悄悄地、缓缓地退居到了一个虚幻的位置上了。这是希腊历史观念的进步所在。事实上,要想在人事中完全排除神的影响,似乎也并不可能。宗教的长期存在,便是印证。与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的著作“人性”色彩更为浓厚。希罗多德在解释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时说:
希腊人从异邦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异邦人从希腊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希腊人又从异邦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这固然是从人的行为上解释历史事件的发生,但却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只是描述了一个现代人看来偶然又表面的现象。修昔底德则与之大不相同。他对现象的观察体现了历史学家应有的睿智和洞察。譬如,他通过对经济力量的分析来揭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内在原因,即雅典势力在希波战争后的急剧增大,引起了斯巴达等其他城邦的不安和恐惧。而科西拉和科林斯两城邦的争执,在修昔底德看来,仅仅是一个表面上的借口。在这里,读者已经无法找到任何难以违抗的天神的意志,也没有不可捉摸的宿命观念,而完完全全是人类、民族、城邦、社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认识,因而具有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
修昔底德能够对历史过程在人性的基础上进行因果分析,首先是因为他对人的力量有了充分的认识。在书中,他借伯里克利(Pericles)之口说道:
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正是因为修昔底德有这种认识,他才能写出在西方脍炙人口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的演说》这一篇章:
在我看来,像这些人一样的死亡,对我们说明了英雄气概的重大意义,不管它是初次表现的也好,或者最后证实的也好。……他们这些人中间,没有人因为想继续享受他的财富而变为懦夫;也没有人逃避这个危难的日子,以图偷生脱离穷困而获得富裕。他们所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要挫败敌人的骄气。……所以他们没有受到别人的责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了战役的冲锋,顷刻间,在他们生命的顶点,也是光荣的顶点,而不是恐惧的顶点,他们就离开我们而长逝了。……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国家和我们全体;至于他们自己,他们获得了永远长青的赞美,最光辉灿烂的坟墓——不是他们遗体所安葬的坟墓,而是他们的光荣永远留在人心的地方。因为著名的人物是把整个地球作为他们的纪念物的……
这里所记录的显然不仅是一段感情真挚的演说而已,而是体现了修昔底德自身的人生观和历史观。
可以这样说,希腊史学在修昔底德那里,形成了一个从神到人的过渡。以后的希腊史学沿之发展,进一步描画了人类活动的一个个历史篇章。
应该看到,修昔底德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念并非无源之水。当时雅典城邦内部民主政治的高度发达,已经形成了一种公民乐于参加政治活动的倾向,在哲学思想上也出现了从研究自然到研究人事的转折,悲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安提戈涅》(Antigone)中已经对人的力量作了赞美:“世界上有许多力量,但是自然中没有什么比人类更为有力。”出身于雅典的修昔底德,自然受到这种人本主义文化的熏陶。他的历史观念,在西方史学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四、战争——当代史的主题
一般人认为,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标志着西方史学的诞生,但是“荷马史诗”所记录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争,仍然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的历史著作都以战争为主题,足以证明这一点。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内容来著述历史,反映了历史学家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历史观念。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的绪论中曾经指出,如果史学家仅仅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付诸于精神作品,就属于“原始的历史”。由于“作家的精神和他所记述的那些动作的精神,是一般无二的”,“所以这种历史的内容不能有十分广大的范围”。按黑格尔的意思,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都属于“原始的历史”。不管黑格尔的判断正确与否,他至少强调了历史观念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制约关系。在古代社会,战争是常见的现象,又是经常能改变人类生活的事件。无论是特洛伊战争、希波战争或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中国的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面貌。因此,战争成为主要的历史现象而首先跃入历史学家的眼帘,毫不足怪。对于希罗多德来说,希波战争是“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而修昔底德则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因此,他“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他们的说法都表明了战争在古代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显然,战争过程的残酷无情、战争胜败的难以预料和战争结果的深切惨痛,足以吸引古代作家对之考察、描画和记述。古代希腊、罗马出现如此多的战争题材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很能证明战争的巨大魅力。
如果说战争题材征服了古代历史学家,使他们写出了流传至今的史学名著,那么反过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之所以在西方史学界受人尊重,亦无法与他们的选题相分离。从史学的发展看问题,这两位公元前5世纪的史学家,正因为选择了同时代的两场战争加以记述,才使他们的著作具有了价值。这不仅是因为战争本身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因为他们记述的是发生于当代的事情。前面已经说过,对历史事实真相的探求是历史学的基础。而在古代,这种探求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只能在耳闻目睹的范围内进行考订。众所周知,口头传闻的真实性,经不起时间的磨损。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著作以同时代的战争(即当代史)为内容,实际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他们记述的可靠性。Peter Gay指出:“由于他(修昔底德)专心致志地只写当代史,范围不广,也就比较容易地达到了信史实录的要求。”这是合乎事实的结论。
尽管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写当代史,但他们有着不同的特点。从记载范围来看,希罗多德视野广阔,万象森列,尽可能地把他所了解的整个“世界”都作了描述。他的《历史》实际上是一幅古代“世界”的立体构画,而在其中,希波战争是中心轴。与此不同,修昔底德则有意识地将史料作了删选,使自己的著作紧紧围绕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程来展开,甚至剔除了一些当时希腊社会的重要史实,使后人扼腕叹息。作为西方史学的奠基之作,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因此各有特点,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修昔底德的主题集中,不蔓不枝,显然著作结构上更为完善。而希罗多德的相对博大,却也为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一个雏形。
希腊史学家选择战争为他们写作历史的主题,反映了战争在古代社会的重大影响,而这一选择又有助于他们在写作时追求真实的意图。如修昔底德就走访了不少战场,搜集了第一手的资料。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过分追求史料的真实性,也会限制历史学家的视野。其结果是,不是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内容进行写作,而是主题内容选择了历史学家。因为战争是人类生活的大事,有关战争的口头传说、遗闻逸事相对要集中和丰富一些,历史学家便会自然而然地随着史料走,只注意战争状况、政治风云而舍弃了其他的内容。古希腊的历史著作大都是战争史、远征记,而没有综合的、触及社会各层次、各方面的通史著作,是一明证。这种情形,至19世纪仍未有大的改变。
希腊史学家视野的相对狭窄,也体现了他们历史方法的原始性。就拿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两部著作来说,他们记载的史料可信范围,也仅限于他们或同时代人的记忆所及的范围之内。修昔底德对史料的批判主要也就是对这一部分史料的考订。而一旦越过这些范围,其可靠性就很难保证了,甚至他们本人对此也不是很有信心。虽然我们对于西方史学发轫阶段的希腊史学不应该有此苛求,但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揭示历史与史学之间的制约关系。
古希腊历史观念的一个最明显的缺陷也许表现在他们的时间观念上。从荷马到修昔底德,希腊人描述不少发生于他们周围的事情,但就时间感而言,却始终未有重大的突破。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已经提到了年和月,偶尔有出现“某某国王统治了多少年”,“过了多少年”等的记载,但就整部著作内容的展开来看,仍然没有事件发展与时间的记录相互交融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在著作中有过这样一段记录:
埃及人在全人类当中第一个想出了用太阳年来记时的办法,并且把一年的形成时期分成十二部分。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是从星辰而得到了这种知识的。在我看来,他们纪年的办法,要比希腊人的办法高明,因为希腊人每隔一年就要插进去一个闰月,才能使季节吻合,但是埃及人把一年分成各有三十天的十二个月,每年之外再加上五天,这样一来,季节的循环就与历法吻合了。希罗多德是个游历家,足迹遍及地中海沿岸的欧、亚、非文明地区。他对埃及太阳历的记载是他亲自考察的结果。从他上面的描述中也可看出,希腊人此时也有了自己的历法,尽管不够精确。但奇怪的是,无论是埃及的太阳历或是希腊的历法,希罗多德在《历史》中都没有加以运用。甚至上面提到的对时间变迁的零星记录,到了书的后半部也愈见稀少。这只能表明,希罗多德尽管接触了不少古代东方的先进文明,却还没有有意识地加以运用。
修昔底德在历史记时方面比希罗多德进了一步。他在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进程时,运用了四季转换来标明战争的延续。但就总体而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间脉络仍不清晰,没有精确的纪年方法。在修昔底德之后,希腊史学仍然没能在时间观念上有所突破。总体来说,希腊史学家选择战争等重大历史题材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叙述方法上对后人的影响甚巨。而且由于他们专心致志于当代历史的探究,更使得历史学的真实性有所保证。但是,希腊半岛各城邦之间分崩离析的状况,又限制了史学家在时空观念上有统一、通贯的眼光。因此,就每一部希腊史学著作来说,它们都各自有其价值,但从宏观的角度察看古希腊的史学观念,则又让人有狭窄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