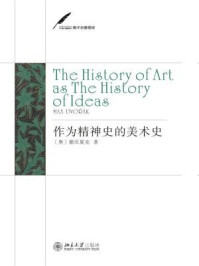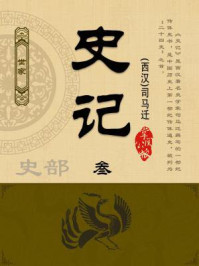诗,是人类文化最初的结晶。
上古时代,蒙昧初开的人们运用瑰丽多姿的想象、富有韵律的语言、神奇怪谲的描绘,创造了一部又一部激荡人心、具有永久魅力的不朽诗篇。中国古代有《诗经》,印度有《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欧洲中世纪有《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和《贝奥武甫》(Beowulf),而“荷马史诗”则是欧洲古代最为久远、最有影响的一部。
“荷马史诗”的产生年代约在公元前12—前8世纪,它共有两部:《伊利亚特》(Iliad,亦译《伊利昂纪》)和《奥德赛》(Odyssey,亦译《奥德修纪》),分别以两个著名的古希腊神话故事为题材,讲述了古希腊诸英雄与特洛伊人(Troy/Trojan)交战以及得胜回朝的经过,为后人记录和描画了古希腊英雄时代的希腊半岛文化发展的状况。
“荷马史诗”是神话,也是传说;是希腊文化的源头,也是西方史学的滥觞。
一、神与人之间
把人类理想中的事物和人物涂抹上一层神奇的色彩,这是各大文明在其幼年时代常见的现象,也是神话产生的基础,表现出一种有趣而又相似的心理状态。但是,把永生的神和凡夫俗子杂糅在一起,共同构成一组组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和宛转曲折的生活情景,却是“荷马史诗”的一大特色。
在“荷马史诗”中,《伊利亚特》讲的是阿开亚人(即希腊人)在统帅阿伽门农(Agamemnon)带领下远征特洛伊,与掠去希腊美女海伦的帕里斯和其他特洛伊人交战的故事。《奥德赛》则讲述了远征特洛伊的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在回乡途中,历经艰难困苦,最后返回家园伊色嘉(Ithaca),杀死向他妻子求婚的王侯们,又成为伊色嘉王的经历。这两个故事讲的似乎都是凡人之间的争斗,但却时时有神参与其间。奥德修斯回家途中,雅典娜女神不时给他以指点,而在《伊利亚特》中,以雅典娜女神为一方,阿波罗为另一方的诸神,不仅直接干预阿开亚人和特洛伊人的战事,而且在诸神之间还爆发了一场战争。诗中这样描绘:
那些不死之神立刻就分成两个敌对的集团,动身前往那行动的场面了。赫拉和帕拉斯、雅典娜向阿开亚人的舰队出发。还有那绕地之神波塞冬,那幸运的赉送者和最巧妙的奇迹制造者赫耳墨斯,也都往那一边走。……向特洛伊人方面走的有戴着闪亮头盔的阿瑞斯、披着头发的福俄玻斯、女神阿耳忒弥斯、勒托、克珊托斯河神,以及爱欢笑的阿佛洛狄忒。群神的出战使得战争的局面大为改观,却并不能为故事本身增色。因为,不死之神之间是不会出现流血、惨死的悲壮场面的。因此,这样的描绘仅见一例。诗中描绘更多的是在诸神的授意下人与人之间的交战。那种凶暴和残忍,那种疯狂和勇猛,体现了古代民族的战争生活,以及他们的人生观、英雄观、价值观。
然而,在“荷马史诗”中,神虽然不常直接参战,但却时时可见。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有神的形象出现。在阿开亚人与特洛伊人停战的时候,宙斯神对雅典娜说:
去看看那些军队,并且想个法儿使得特洛伊人趁阿开亚人得胜的时候去攻击他们,从而破坏停战。在战斗进行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人对神祷告,以求得神的帮助;在战败的时候,又在神的帮助下逃脱战场,躲避伤害。如阿佛洛狄忒救她儿子埃涅阿斯。总之,正如诗中所说:
只消一刻儿工夫,神就可以使得一个勇敢的人吃败仗逃走,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又唆使他去战斗了。这种人力无可挽回的神意以及它的无处、无时不在,实际上是古代人对自然界崇拜的形象化反照。所以“荷马史诗”中的主要人物,不仅是阿喀琉斯(Achilleus)、阿伽门农、奥德修斯、赫克托尔(Hector)等诸位英雄,雅典娜、阿波罗,甚至赫拉、宙斯都是诗篇的主要角色。神、人之间的交流和呼应,如同交响乐的两部主题,共同展开这两部诗篇的主要情节。
如果说,在人类活动的关键时刻出现神的干预是一种对自然力量的迷信和膜拜,那么把神拉进人的活动中间,与人类共同组成生活,则同时又可视为一种对人性、人力的尊重和拔高。神的人化和人的神化是不可或缺的两方面。“荷马史诗”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反映了当时人的生活理想,即他们对自身生活的态度。
在“荷马史诗”中,神与人产生爱情的事例比比皆是。如奥德修斯就曾经两度和女神相恋、同居,而诗篇中的大部分英雄,都是神人结合所生的。他们尽管不能永生,却具有凡人无法企及的本领和力量。因此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敢于和神交战。在《伊利亚特》中,狄俄尼索斯和阿喀琉斯都有这样的本事。狄俄尼索斯在战斗中击伤了女神阿佛洛狄忒与人所生的儿子埃涅阿斯,阿佛洛狄忒赶来救援,她虽然救出了埃涅阿斯,自己却因为懦弱无能而被狄俄尼索斯刺伤了。这样的例子尽管罕见,却已足以说明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之间并不具有恒常的尊卑、高下关系。
在享受生活方面,神与人之间的差异更不明显。虽然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群神生活极其优裕、奢侈,但人间的乐园也同样豪华富贵。《奥德赛》中对腓尼基国王阿吉诺的宫殿有如下一段描述:
阿吉诺的高大宫殿闪耀着光芒,有如太阳或月亮一样。从门口到宫殿有好多重铜墙,上面盖着碧琉璃瓦,黄金的大门紧护着精筑的宫室,在青铜门阀两旁立着银铸的门柱,上面的门楣也是银镶的,门环由黄金制成,两旁还有金银浇铸的狗,那是赫费耶特的巧艺创作,用来看守高贵的阿吉诺的宫殿;这两只狗千古常存,长生不老。“荷马史诗”中对人间生活的讴歌,竭尽了赞美之词,比想象中的神的生活毫不逊色。
甚至,当奥德修斯受到了女神加里普索的一再挽留时,他并不因为对方是女神而自己的妻子珀涅罗珀是凡人而忘却人世。相反,他说道:
尊贵的女神,请你不要为这件事生气,这一切我自己也晓得,聪明的珀涅罗珀在身材和容貌上都比不过你;她不过是个凡人,你却长生不老。可是我还是天天怀念,想要回家,想看到还乡的那一天……
这样的回答在大部分古代神话、传说中并不多见。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古希腊人注重现世生活的突出印象。
“荷马史诗”中对神、人关系的表述,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古希腊人的人生观,特别是对现实生活的看法。而现实从来不能与历史相脱离。因此,这种看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观念的一个部分。对我们来说,史诗中对神或人的具体刻画并不太重要,但从中透露出的当时人的生活态度,却是颇具吸引力的:那是一种既承认神的决定作用,又充分尊重人的力量,赞颂人间生活,推崇人世英雄的意识;那是一种人与神共同创造的“历史”。于是在许许多多神奇怪诞的现象背后,人的形象已经开始露面了,虽然他与高大的神相比,还是那样黯淡微弱,时隐时现。
二、无始无终的“历史”
神和人是“荷马史诗”的主角。但是,这里的人显然不是涵括一切的概念,而是一部分贵族化的英雄,是一些半神半人的人物。《伊利亚特》中的所有人物,无论是贯穿全篇的阿喀琉斯、赫克托尔,抑或是只露一面便结束生命的小角色,都具有显赫的出身、名贵的家世,这在《伊利亚特》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奥德赛》还描述了几个奴隶,但在史诗的作者看来,奴隶的地位是等同于猪、狗、牛等畜牲的。因此,“荷马史诗”是一部以贵族为中心的作品,是“英雄”的史诗,而不是一般平民的日常生活记录。
于是,“荷马史诗”便显露出了它的一个致命缺陷:没有时间概念。这里面的道理可能是因为对那些半神半人、高人一等的英雄来说,时间并不重要,生命的流逝似乎微不足道。譬如《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和《奥德赛》中的主人翁奥德修斯,尽管他们也算是人类,然而看他们的行为,却似乎是长生不老的。奥德修斯经历了特洛伊战争的磨难,在回乡途中又饱经风霜,但却丝毫不显老态,仍然是智慧超群、勇猛过人。甚至于他的妻子珀涅罗珀,也几乎成了天上永生的女神。尽管生儿育女,岁月流转,却是青春永驻,风韵依然,求婚者络绎不绝。史诗中甚至把求婚者们的骚扰,珀涅罗珀的忠贞,帖雷马科(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之子)的苦恼和奥德修斯的复仇当做贯穿《奥德赛》的主线。这种毫无时间概念的描述,在现代人看来,有点滑稽,然而在史诗作者的笔下,却又显得“合情合理”。因为史诗要歌颂的,正是这样的超人的英雄,是理想中的“人”,而不是一般的凡人。
《奥德赛》中提到时间有一句多次出现的话:“当那初升的有红指甲的曙光刚刚呈现的时候”,紧接在下面的就是英雄开始的新的征程、新的奋斗。一天的辛劳结束,便再来一句套语:“夜幕降临,黑暗笼罩大地。”英雄休息了,进入梦乡。这样重复的周转,套语一再地使用,这从文学鉴赏的眼光考察,自有其修辞学上的作用,甚至起“画龙点睛”的效果。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只能说明“荷马史诗”在时间观念上除了昼夜之分以外,没有更进一步的概念,特别是缺少时间前后延续的观念,看不到一天与一天之间的差异和进化,也没有明显的四季轮换的记述。换句话说,我们在“荷马史诗”中除了见到时间在一日一日地流逝之外,无法捕捉到把这些日子累积并划分为年月的任何企图。整部诗篇是“无始无终”的,虽然它在故事发展情节上有着一定的完整性。
缺乏时间的延续性和阶段性这一缺陷,在《伊利亚特》中表现尤其明显。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特洛伊战争持续时间大致为十年。但是在《伊利亚特》中,却使人无法得出这一印象,似乎战争只是进行了几个星期。对交战双方英雄和众神之间的纠葛的详细描写,淹没了历史学家最关心的时间记录。这使人不能不强烈地意识到“荷马史诗”在总体上的文学色彩。它是一部在人类文明刚刚崭露曙光时期的神话与传说的杂糅体。
造成这部史诗缺少时间观念的最大原因,无疑是它的“贵族化”特征。无论是特洛伊人还是阿开亚人,其主要角色都是部落首领一类的人物。对于他们来说,时间的重要意义显然比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辛勤劳作的普通平民要微小得多。而记录普通平民的生活,这本身也不是“荷马史诗”的主旨。我们也无法对此苛求。
希腊半岛的地理环境,与以大河流域为特征的古代东方文明发祥地很不相同。农业生产在希腊并不占重要地位。相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古埃及人民在对尼罗(Nile)河水的涨落的考察中,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历法——对时间的记录和划分。显然,古埃及人的时间观念要强于希腊人,而希腊人在时间观念上的落后,还要再持续好几个世纪。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表明,在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中,前者比较注重人和自然的联系,而后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腊早期没有出现编年史,亦可见希腊人时间观念上的薄弱;或者说,古希腊社会并不需要这种逐年记录的“历史”。
不过,从历史学发展的角度着眼,对时间的疏漏毕竟是“荷马史诗”的不足,同时也是在它之后的大部分古希腊史学作品的不足。现代人已经认识到,时间感是历史感的基础。没有时间感的历史著作,如柯林伍德(Robin Collingwood)所言,只是一种“半历史”(quasi—history)。
三、有头有尾的叙述
“荷马史诗”在时间观念上的薄弱还不能影响它作为欧洲史学源头的地位。史诗叙述体裁的完整、事件发展的连贯和线索脉络的清晰,都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来史学家的楷模。可以这样说,希腊史学对叙述体裁的重视和掌握,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荷马史诗”的熏染,而史学叙述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发展和流行,又与希腊史学家的努力有密切联系。
在写作体裁上,“荷马史诗”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故事情节的完整和紧凑。《伊利亚特》开头便点出了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的争吵,把他们两人作为事件发展的主线。以后尽管也用较多笔墨描写了特洛伊人主将赫克托尔的为人、战绩和阵亡,交代了阿开亚人和特洛伊人争战的过程,但其主要注意力仍然没有从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身上移开。他们两人的争执与和解始终是阿开亚方面举足轻重的因素,甚至也是阿开亚人最终得胜的决定因素。因为正是他们两人的和解和阿喀琉斯的出战,才使得战争的局面有了改观,也正是阿喀琉斯才杀死了特洛伊人的英雄赫克托尔。毫无疑问,阿喀琉斯是《伊利亚特》中最主要的人物,把这位超乎寻常的英雄作为叙述的中心,自然反映了作者的理想。但就体裁而言,这种方法却使得《伊利亚特》不仅通篇连贯、内容完整,而且脉络清楚、中心突出。
与《伊利亚特》相比,《奥德赛》在内容和人物上似乎更加集中、单一,这也表现出某种发展。《奥德赛》通篇讲的就是奥德修斯回归故土、施计复仇的过程,没有任何枝枝蔓蔓的情节。主要人物也自然而然是奥德修斯,其余的人都只是作为陪衬而存在。本来帖雷马科外出寻父可以成为一条副线,但这条副线并没有深入展开,而是让奥德修斯和帖雷马科很快团聚在一起了。这样,整篇史诗可说是层层展开,丝丝入扣,主题很鲜明,人物也集中,这在古代作品中,实属罕见。
主题鲜明、内容连贯,这不仅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要求,同时也是历史著作的衡量标准之一。而在古代,文学与史学的区别并不明显。古希腊更是如此。“荷马史诗”既是希腊文学又是希腊史学的本源。“荷马史诗”对古希腊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历史体裁上。纵观古希腊史学,几乎没有用编年体写成的著作,绝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是将人物、事件和历史过程掺合在一起加以综合记述的“叙述体”。这是古希腊史学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贯穿整个西方史学的一条主脉。显然,这一叙述体裁最早的模式,就来自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特别是后者)在内容上的连贯和集中,甚至超过了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4—约前425年)的《历史》(Histories)。这些都足以证实“荷马史诗”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了。
编年体和叙述体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不同。实际上,这里也反映出历史意识上的差别。上面已经说过,古希腊人较之古代东方的居民来说,更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较少注意自然对人的控制。又加上他们缺乏严格的时间观念,这就很自然地使得古希腊没有产生逐年记事的编年史。而反过来,对于人际关系的注重,又使得他们创造了一种最适合于表达这种关系的叙述体裁。如果从西方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这一叙述体裁可谓垂之久远,应该说是成功的。它既能以其故事情节取悦读者(事实上在那时大部分是听众。直到希罗多德的时代,历史著作的流传也主要靠生动的讲述),又能展开那种人与人之间智慧的较量、流血的斗殴,表现生与死、爱与恨的痛苦和欢乐。要想把这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的确不能像孔子编《春秋》那样单靠“微言大义”的笔法来解决。就这一点来说,“荷马史诗”在体裁上对希腊史学的巨大影响,本身又适应了希腊社会的需要,表现出希腊人独特的历史观念。
然而,叙述体裁本身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荷马史诗”的叙述方式更有其原始、幼稚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史诗作者还不能真正地把人的活动始终放在叙述的主题,而往往把人的行为和神的意志加以糅合。因此,尽管史诗就人的活动方面没有“副线”,但却常常有神的活动这样一条“副线”穿插其内。这一缺点明确地揭示出神话与历史之间的距离。
四、天命不可违
我们说古希腊人比较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表示他们不畏惧自然界的力量,无视自然界对人的影响。事实上这在古代社会是不可能的。社会生产条件的落后使得人在自然面前常常感到无能为力,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常常产生巨大影响。这让古代社会的居民对自然界的一举一动既感到神秘,又充满恐惧。这种复杂的情感往往以迷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们无法解答在人力不可企及的地方存在着什么力量,于是便塑造出一个个威力无比、各司其职的神,作为问题的答案和膜拜朝奉的对象。而这些诸神的集合作用,便被笼统地表示为“天命”或者“命运”。“荷马史诗”中关于这些内容的叙述,俯拾皆是。
在《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经过几天的漂泊,来到了腓尼基的国土。腓尼基王国公主瑙西卡娅发现了他。奥德修斯对她说了一大段话:
就是昨天,我才从葡萄紫的海水中逃脱;命运把我送到这里,也许还要我受一些苦;我的苦难还没有到头,天神们恐怕还要我受很多苦……
瑙西卡娅回答道:
外乡人,看来你不像是一个坏人或糊涂人,奥林匹斯山的宙斯按照他的意旨,给好人和坏人降福降灾;你的命运是他决定的,你只好忍受吧。受苦由天命决定,那么享福也自然离不开神的照应。奥德修斯与帖雷马科父子相认的时候,女神雅典娜为奥德修斯点触了一下,顿时使他容光焕发,帖雷马科大为惊奇。奥德修斯说道:
是猎护之神雅典娜让我改变了形状;这是她的主意,因为她有能力把人一时变得像乞丐一样,一时又变成穿着美好服装的年轻人;主掌广天的神做这些事很容易;他们可以使一个凡人高贵,也可以使他卑贱。在荷马时代的人们眼中,甚至特洛伊战争也是由天神布置的,由此可以供给后人歌唱的材料。至于那些细枝末节的神意的干预,更是不胜枚举。
除了用天神参与人世来表达天命的权威之外,“荷马史诗”的作者还运用自然界发生的某些奇异现象作为体现命运的朕兆。《伊利亚特》第十二卷有这样一段描写:特洛伊人的队伍正要出发,队伍前方的左侧上空出现了一只老鹰,爪里抓着一条血红色的蛇。忽然,蛇转过身子去咬那只老鹰头颈旁边的胸部,那只老鹰痛得把爪松开来,让那条蛇落在了队伍里,然后就大叫一声乘风而去了。特洛伊人认为这是一个凶兆,因此为进军还是撤退的问题引起了一番争执。在《奥德赛》中,也有这样的描写:奥德修斯回到家中,在准备收拾那些求婚者之前,先与他们比试本领。这时天边不断响起雷声,奥德修斯认为这是天神宙斯给他的吉兆,顿时精神振奋,勇气倍增。像这样把自然现象加以人为解释,并赋予命运的象征意义,实际上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流露。朕兆的吉凶似乎是不可捉摸的,但最后仍与人的活动的成败密切相关。
因此,这里面就透露了古希腊人对于历史进程的最初看法。历史无非是人的活动的记录和再现,对于人及其努力的结果持有什么看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观念的一部分。“荷马史诗”表露出来的浓厚的命运观念,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自然力的崇拜和对人力的疑惑。这在人类的古代文明中颇为常见,表明人尚未从自然力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仍然受命于自然。
但是,“荷马史诗”在精神上毕竟是洋溢着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众多的英雄在战争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朝气和力量,强烈的爱憎和人情,表明他们绝不仅仅是匍匐在命运脚下的可怜虫,而是拥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也许是因为史诗这一形式本身便具有抒情和浪漫的特质,笼罩于“荷马史诗”中的整个精神也同样是浪漫的、向上的、理想的。在这样的氛围中,命运尽管威力无比,无可违逆,但却总是赐福于那些英雄的。而那些英雄自己,也仿佛能领悟到自己的命运所向。譬如,奥德修斯在回乡途中虽经磨难,但他认为天命只不过是要让他多承受一些痛苦而已。阿喀琉斯更是具有异常的神力。在《伊利亚特》中,他的出场往往具有天命所归的威力。他自己也充满必胜的信念。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命运的盲目尊崇是古代社会屡见不鲜的现象。但是,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形式又是各不相同的。“荷马史诗”产生于一个特定的时代,为古希腊特有的英雄时代。当时的人们对于命运、自然、人力的理解,都涂抹上了一层“英雄”色彩。这样一个特定时代所产生出来的历史观念,在其他民族中并不多见。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共工、夸父、后羿等英雄,但他们最终的结局往往是悲剧,这无疑是显著的差别。
要知道,即使在希腊本土,这样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也是一去不返的。在以后的希腊史学著作中,很少再有这种回肠荡气的英雄气概和无拘无束的大胆想象了。命运的观念却仍然存在;人物逐渐变得渺小,却似乎更为真实。事件的组合少了戏剧性冲突,却更接近于现实的生活。于是,神话便开始转变为历史,西方的历史学便在这种朴实无华的风格中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