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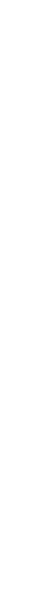
|
第一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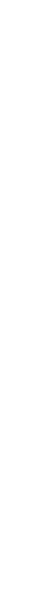
|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
昨夜响了一宵倒塌的声音,轰然声连接着轰然声,仿佛一幢一幢房屋疲惫不堪之后躺下了。我在持续的轰然声里似睡非睡,天亮后打开屋门时轰然声突然消失,我开门的动作似乎是关上轰然声的开关。随后看到门上贴着这张通知我去殡仪馆火化的纸条,上面的字在雾中湿润模糊,还有两张纸条是十多天前贴上去的,通知我去缴纳电费和水费。
我出门时浓雾锁住了这个城市的容貌,这个城市失去了白昼和黑夜,失去了早晨和晚上。我走向公交车站,一些人影在我面前倏忽间出现,又倏忽间消失。我小心翼翼走了一段路程,一个像是站牌的东西挡住了我,仿佛是从地里突然生长出来。我想上面应该有一些数字,如果有203,就是我要坐的那一路公交车。我看不清楚上面的数字,举起右手去擦拭,仍然看不清楚。我揉擦起了自己的眼睛,好像看见上面的203,我知道这里就是公交车站。奇怪的感觉出现了,我的右眼还在原来的地方,左眼外移到颧骨的位置。接着我感到鼻子旁边好像挂着什么,下巴下面也好像挂着什么,我伸手去摸,发现鼻子旁边的就是鼻子,下巴下面的就是下巴,它们在我的脸上转移了。
浓雾里影影幢幢,我听到活生生的声音此起彼伏,犹如波动之水。我虚无缥缈地站在这里,等待203路公交车。听到很多汽车碰撞的声响接踵而来,浓雾湿透我的眼睛,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听到连串车祸聚集起来的声响。一辆轿车从雾里冲出来,与我擦肩而去,冲向一堆活生生的声音,那些声音顷刻爆炸了,如同沸腾之水。
我继续站立,继续等待。过了一会儿,我心想这里发生大面积的车祸,203路公交车不会来了,我应该走到下一个车站。
我向前走去,湿漉漉的眼睛看到了雪花,在浓雾里纷纷扬扬出来时恍若光芒出来了,飘落在脸上,脸庞有些温暖了。我站住脚,低头打量它们如何飘落在身上,衣服在雪花里逐渐清晰起来。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死去的第一天。可是我没有净身,也没有穿上殓衣,只是穿着平常的衣服,还有外面这件陈旧臃肿的棉大衣,就走向殡仪馆。我为自己的冒失感到羞愧,于是转身往回走去。
飘落的雪花让这个城市有了一些光芒,浓雾似乎慢慢卸妆了,我在行走里隐约看见街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我走回到刚才的公交车站,一片狼藉的景象出现在眼前,二十多辆汽车横七竖八堵住了街道,还有警车和救护车;一些人躺在地上,另一些人被从变形的车厢里拖出来;有些人在呻吟,有些人在哭泣,有些人无声无息。这是刚才车祸发生的地点,我停留一下,这次确切看清了站牌上的203。我穿越了过去。
我回到出租屋,脱下身上不合时宜的衣服,光溜溜走到水槽旁边,拧开水龙头,用手掌接水给自己净身时看到身上有一些伤口。裂开的伤口涂满尘土,里面有碎石子和木头刺,我小心翼翼把它们剔除出去。
这时候放在床上枕头旁边的手机响了,我感到奇怪,因为欠费已被停机两个月,现在它突然响了。我拿起手机,摁了一下接听键,小声说: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你是杨飞吗?”
“是我。”
“我是殡仪馆的,你到哪里了?”
“我在家里。”
“在家里干什么?”
“我在净身。”
“都快九点钟了,还在净身?”
我不安地说:“我马上来。”
“快点来,带上你的预约号。”
“预约号在哪里?”
“贴在你的门上。”
对方挂断电话。我心里有些不快,这种事情还要催促?我放下电话,继续清洗身上的伤口。我找来一只碗,用碗接水后冲刷那些残留在伤口里的碎石子和木头刺,清洗速度加快了。
净身之后,我湿漉漉走到衣柜那里,打开柜门寻找我的殓衣。里面没有殓衣,只有一身绸缎的白色睡衣像是殓衣,上面有着隐隐约约的印花图案,胸口用红线绣上的“李青”两字已经褪色,这是那段短暂婚姻留下的痕迹。我当时的妻子李青在商店里精心挑选了两套中式对襟睡衣,她在自己的睡衣胸口绣上我的名字,在我的睡衣胸口绣上她的名字。那段婚姻结束之后,我没再穿过它,现在我穿上了,感到这白色的绸缎睡衣有着雪花一样温暖的颜色。
我打开屋门,仔细辨认贴在门上的殡仪馆通知,上面有一个“A3”,心想这就是预约号。我将通知摘下来,折叠后小心放入睡衣口袋。我准备走去时觉得缺少了什么,站在飘扬的雪花里思忖片刻,想起来了,是黑纱。我孤苦伶仃,没有人会来悼念我,只能自己悼念自己。
我返回出租屋,在衣柜里寻找黑布。寻找了很久,没有黑布,只有一件黑色的衬衣,因为陈旧,黑色已经趋向灰黑色。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剪下它的一截袖管,套在左手的白色袖管上。虽然自我悼念的装束美中不足,我已经心满意足。
我的手机又响了。
“杨飞吗?”
“是我。”
“我是殡仪馆的,”声音问,“你想不想烧啊?”
我迟疑了一下说:“想烧。”
“都九点半了,你迟到啦。”
“这种事情也有迟到?”我小心问。
“想烧就快点来。”
殡仪馆的候烧大厅宽敞深远,外面的浓雾已在渐渐散去,里面依然雾气环绕,几盏相隔很远的蜡烛形状的壁灯闪烁着泛白的光芒,这也是雪花的颜色。不知为何,我见到白色就会感到温暖。
大厅的右边是一排排被铁架子固定住的塑料椅子,左边是沙发区域,舒适的沙发围成几个圆圈,中间的茶几上摆放着塑料花。塑料椅子这边坐着很多候烧者,沙发那边只有五个候烧者,他们舒适地架着二郎腿,都是一副功成名就的模样,塑料椅子这边的个个都是正襟危坐。
我进去时一个身穿破旧蓝色衣服戴着破旧白手套的骨瘦如柴的人迎面走来,我觉得他的脸上只有骨头,没有皮肉。
他看着我五官转移之后的脸轻声说:“您来了。”
我问他:“这是火葬场吗?”
“现在不叫火葬场了,”他说,“现在叫殡仪馆。”
我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就像是进入一家宾馆后询问:这里是招待所吗?
他的声音里有着源远流长的疲惫,我听出来他不是给我打电话说“我是殡仪馆的”那位。我为自己的迟到道歉,他轻轻摇摇头,用安慰的语调说今天有很多迟到的。我的预约号已过期作废,他走到入门处的取号机上为我取号,然后将一张小纸片交给我。
我从A3推迟到A64,这个号码上面显示在我前面等候的有54位。
我问他:“今天还能烧吗?”
“每天都有不少空号。”他说。
他戴着破旧白手套的右手指向塑料椅子这边,意思是让我去那里等候,我的眼睛看着沙发那边。他提醒我沙发那边是贵宾区域,我的身份属于塑料椅子这边的普通区域。我手里拿着A64号走向塑料椅子这里时,听到他自言自语的叹息之声:
“又一个可怜的人,没整容就来了。”
我坐在塑料椅子里。这位身穿蓝色衣服的在贵宾候烧区域和普通候烧区域之间的通道上来回踱步,仿佛深陷在沉思里,他脚步的节奏像是敲门的节奏。不断有迟到的进来,他迎上去说声“您来了”,为他们重新取号,随后伸手一指,让他们坐到我们这边的塑料椅子上。有一个迟到的属于贵宾,他陪同到沙发那边的区域。
塑料椅子这边的候烧者在低声交谈,贵宾区域那边的六个候烧者也在交谈。贵宾区域那边的声音十分响亮,仿佛是舞台上的歌唱者,我们这边的交谈只是舞台下乐池里的伴奏。
贵宾区域里谈论的话题是寿衣和骨灰盒,他们身穿的都是工艺极致的蚕丝寿衣,上面手工绣上鲜艳的图案,他们轻描淡写地说着自己寿衣的价格,六个候烧贵宾的寿衣都在两万元以上。我看过去,他们的穿着像是宫廷里的人物。然后他们谈论起各自的骨灰盒,材质都是大叶紫檀,上面雕刻了精美的图案,价格都在六万元以上。他们六个骨灰盒的名字也是富丽堂皇:檀香宫殿、仙鹤宫、龙宫、凤宫、麒麟宫、檀香西陵。
我们这边也在谈论寿衣和骨灰盒。塑料椅子这里说出来的都是人造丝加上一些天然棉花的寿衣,价格在一千元上下。骨灰盒的材质不是柏木就是细木,上面没有雕刻,最贵的八百元,最便宜的两百元。这边骨灰盒的名字却是另外一种风格:落叶归根、流芳千古。
与沙发那边谈论自己寿衣和骨灰盒的昂贵不同,塑料椅子这边比较着谁的价廉物美。坐在我前排的两位候烧者交谈时知道,他们是在同一家寿衣店买的同样的寿衣,可是一个比另一个贵了五十元。买贵了的那位唉声叹气,喃喃自语:
“我老婆不会讲价。”
我注意到塑料椅子这边的候烧者也都穿上了寿衣,有些身穿明清风格的传统寿衣,有些身穿中山装或者西装的现代寿衣。我只是穿上陈旧的白色中式对襟睡衣,我庆幸早晨出门时意识到臃肿的棉大衣不合适,换上这身白色睡衣,虽然寒碜,混在塑料椅子这里也能滥竽充数。
可是我没有骨灰盒,我连落叶归根和流芳千古这样的便宜货也没有。我开始苦恼,我的骨灰应该去哪里?撒向茫茫大海吗?不可能,这是伟人骨灰的去处,专机运送军舰护航,在家人和下属的哭泣声中飘扬入海。我的骨灰从炉子房倒出来,迎接它们的是扫帚和簸箕,然后是某个垃圾桶。
坐在身旁的一位老者扭头看见了我的脸,惊讶地问:“你没有净身,没有整容?”
“净身了,”我说,“我自己净身的。”
“你的脸,”老者说,“左边的眼珠都出去了,鼻子歪在旁边,下巴这么长。”
我想起来净身时忘记自己的脸了,惭愧地说:“我没有整容。”
“你家里人太马虎了,”老者说,“没给你整容,也没给你化妆。”
我是孤零零一个人。给予我养育之恩的父亲杨金彪一年多前身患绝症不辞而别,我的生父生母远在千里之外的北方城市,他们不知道此时此刻我已置身另外一个世界。
坐在另侧身旁的一个女人听到我们的谈话,她打量起了我的衣着,她说:“你的寿衣怎么像睡衣?”
“我穿的是殓衣。”我说。
“殓衣?”她有些不解。
“殓衣就是寿衣,”老者说,“寿衣听上去吉利。”
我注意到了他们两个的脸,都是浓妆艳抹,好像要去登台表演,而不是去炉子房火化。
前面的塑料椅子里有一个候烧者对身穿蓝色衣服的抱怨起来:“等了这么久,也没听到叫号。”
“正在进行市长的遗体告别仪式,”身穿蓝色衣服的说,“早晨烧了三个就停下了,要等市长进了炉子房,再出去后,才能轮到您们。”
“为什么非要等到市长烧了,才烧我们?”那个候烧者问。
“这个我不知道。”
另一个候烧者问:“你们有几个炉子?”
“两个,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国产的。进口的为贵宾服务,国产的为您们服务。”
“市长是不是贵宾?”
“是。”
“市长要用两个炉子烧吗?”
“市长应该用进口炉子。”
“进口炉子已经留给市长了,国产炉子为什么还要留着?”
“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两个炉子都停了。”
沙发区域那边有贵宾向身穿蓝色衣服的招招手,他立即快步走去。
那个贵宾问他:“市长的遗体告别还有多久?”
“我不太清楚,”他停顿一下说,“估计还有一会儿,请您耐心等候。”
一个迟到的候烧者刚刚进来,听到他们的对话,站在通道上说:
“市里大大小小的官员,还有各区县大大小小的官员,一千多人,一个一个向市长遗体告别,还不能走快了,要慢慢走,有的还要哭上几声。”
“一个市长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贵宾很不服气地说。
这个迟到的继续说:“早晨开始,城里的主要道路就封锁了,运送市长遗体的车开得跟走路一样慢,后面跟着几百辆给市长送行的轿车,半小时的路可能要走上一个半小时。现在主要道路还在封锁,要等到市长的骨灰送回去以后,才会放行。”
城里主要道路封锁了,其他的道路也就车满为患。我想起早晨行走在浓雾里连串的车祸声响和此后看到的一片狼藉景象。随即我又想起半个月前报纸电视上都是市长突然去世的消息,官方的解释是市长因为工作操劳过度突发心脏病去世。网上流传的是民间的版本,市长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行政套房的床上,与一个嫩模共进高潮时突然心肌梗塞,嫩模吓得跑到走廊上又哭又叫,忘记自己当时是光屁股。
然后我听到沙发那边的贵宾谈论起了墓地,塑料椅子这边也谈论起了墓地。塑料椅子这边的都是一平米的墓地,沙发那边的墓地都在一亩地以上。或许是那边听到了这边的议论,沙发那边一个贵宾高声说:
“一平米的墓地怎么住?”
塑料椅子这边安静下来,开始聆听沙发那边令人瞠目的奢华。他们六个中间有五个的墓地都建立在高高的山顶,面朝大海,云雾缭绕,都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海景豪墓。只有一个建立在山坳里,那里树林茂密溪水流淌鸟儿啼鸣,墓碑是一块天然石头,在那里扎根几百上千年了,他说现在讲究有机食品,他的是有机墓碑。另外五个的墓碑有两个是实体的缩小版,一个是中式庭院,一个是西式别墅;还有两个是正式的墓碑,他们声称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最后一个说出来让大家吃了一惊,他的墓碑竟然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而且尺寸大小一样,只是纪念碑上面毛泽东手迹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改成了“李峰同志永垂不朽”,也是毛泽东的手迹,是他的家人从毛泽东的手迹里面找出来“李峰同志”四个字,放大后刻到墓碑上面。
他补充道:“李峰同志就是我。”
有一个贵宾对他说:“这个有风险,说不定哪天被政府拆了。”
“政府那边已经花钱搞定,”他胸有成竹地说,“只是不能让记者曝光,我的家属已经派出十二人对记者严防死守,十二个人刚好是部队一个班的编制,有一个警卫班保护我,我可以高枕无忧。”
这时候烧大厅的两排顶灯突然亮了,黄昏时刻变成正午时刻,身穿蓝色衣服的这位急忙走向大门。
市长进来了,他一身黑色西装,里面是白色衬衣,系着一根黑色领带。他面无表情地走过来,脸上化了浓妆,眉毛又黑又粗,嘴唇上抹了鲜艳的口红。身穿蓝色衣服的迎上去,殷勤地指引他:
“市长,请您到豪华贵宾室休息一下。”
市长微微点点头,跟随身穿蓝色衣服的向前走去,大厅里面有两扇巨大的门徐徐打开,市长走进去之后,两扇门徐徐合上。
沙发那边的贵宾们没有了声音,豪华贵宾室镇住了沙发贵宾区,金钱在权力面前自惭形秽。
我们塑料椅子这边的声音仍然在起伏,谈论的仍然是墓地。大家感慨现在的墓地比房子还要贵,地段偏远又拥挤不堪的墓园里,一平米的墓地竟然要价三万元,而且只有二十五年产权。房价虽贵,好歹还有七十年产权。一些候烧者愤愤不平,另一些候烧者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二十五年以后怎么办?二十五年后的墓地价格很可能贵到天上去了,家属无力续费的话,他们的骨灰只能去充当田地里的肥料。
坐在前排的一个候烧者伤心地说:“死也死不起啊!”
我身旁的那位老者平静地说:“不要去想以后的事。”
老者告诉我,他七年前花了三千元给自己买了一平米的墓地,现在涨到三万元了。他为自己当初的远见高兴,如果是现在,他就买不起墓地了。
他感慨道:“七年涨了十倍。”
候烧大厅里开始叫号了。显然市长已经烧掉,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党旗,安放在缓缓驶去的黑色殡仪车里,后面有几百辆轿车缓缓跟随,被封锁的道路上哀乐响起……贵宾号是V字头的,普通号是A字头的,我不知道市长级别的豪华贵宾号是什么字母打头,可能豪华贵宾不需要号码。
属于V的六个贵宾都进去了,属于A的叫得很快,就如身穿蓝色衣服的所说,有很多空号,有时候一连叫上十多个都是空号。这时候我发现身穿蓝色衣服的站在我旁边的走道上,我抬起头来看他时,他疲惫的声音再次响起:
“空号的都没有墓地。”
我没有骨灰盒,没有墓地。我询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听到了A64,这是我的号码,我没有起身。A64叫了三遍后,叫A65了,身旁的女人站了起来,她穿着传统寿衣,好像是清朝的风格,走去时两个大袖管摇摇摆摆。
身旁的老者还在等待,还在说话。他说自己的墓地虽然有些偏远,交通也不方便,可是景色不错,前面有一片不大的湖水,还有一些刚刚种下的树苗。他说自己去了那里以后不会出来,所以偏远和交通不方便都不是问题。然后他打听我的墓地是在哪个墓园。
我摇摇头说:“我没有墓地。”
“没有墓地,你到哪里去?”他惊讶地问。
我感到自己的身体站了起来,身体带着我离开了候烧大厅。
我重新置身于弥漫的浓雾和飘扬的雪花里,可是不知道去哪里。我疑虑重重,知道自己死了,可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我行走在若隐若现的城市里,思绪在纵横交错的记忆路上寻找方向。我思忖应该找到生前最后的情景,这个最后的情景应该在记忆之路的尽头,找到它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死亡时刻。我的思绪借助身体的行走穿越了很多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的情景之后,终于抵达了这一天。
这一天,似乎是昨天,似乎是前天,似乎是今天。可以确定的是,这是我在那个世界里的最后一天。我看见自己迎着寒风行走在一条街道上。
我向前走去,走到市政府前的广场。差不多有两百多人在那里抗议暴力拆迁,他们没有打出抗议的横幅,没有呼喊口号,只是在互相讲述各自的不幸。我听出来了,他们是不同强拆事件的受害者,我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一位老太太流着眼泪说她只是出门去买菜,回家后发现自己的房子没有了,她还以为走错了地方。另外一些人在讲述遭遇深夜强拆的恐怖,他们在睡梦中被阵阵巨响惊醒,房屋摇晃不止,他们以为是发生了地震,仓皇逃出来时才看到推土机和挖掘机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有一个男子声音洪亮地讲述别人难以启口的经历,他和女友正在被窝里做爱的时候,突然房门被砸开了,闯进来几个彪形大汉,用绳子把他们捆绑在被子里,然后连同被子把他们两个抬到一辆车上,那辆汽车在城市的马路上转来转去,他和女友在被捆绑的被子里吓得魂飞魄散,不知道汽车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汽车在这个城市转到天亮时才回到他们的住处,那几个彪形大汉把他们从汽车里抬出来扔在地上,解开捆绑他们的绳子,扔给他们几件别人的衣服,他们两个在被子里哆嗦地穿上了别人的衣服,有几个行人站在那里好奇地看着他们,他们穿上衣服从被子里站起来时,他看到自己的房屋已经夷为平地,他的女友呜呜地哭上了,说以后再也不和他睡觉了,说和他睡觉比看恐怖电影还要恐怖。
他告诉周围的人,房屋没有了,女友没有了,他的性欲在那次惊吓里也是一去不回。他伸出四根手指说,为了治疗自己的阳痿已经花去四万多元,西药中药正方偏方吃了一大堆,下面仍然像是一架只会滑行的飞机。
有人问他:“是不是刚起飞就降落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他说,“只会滑行,不会起飞。”
有人喊叫:“让政府赔偿。”
他苦笑地说:“政府赔偿了我被拆掉的房屋,没赔偿我被吓跑的性欲。”有人建议:“吃伟哥吧。”
他说:“吃过,心脏倒是狂跳了一阵,下面还是只会滑行。”
我在阵阵笑声里走了过去,觉得他们不像是在示威,像是在聚会。我走过市政府前的广场,经过两个公交车站,前面就是盛和路。
那个时刻我走在人生的低谷里。妻子早就离我而去,一年多前父亲患上不治之症,为了给父亲治病,我卖掉房屋,为了照顾病痛中的父亲,我辞去工作,在医院附近买下一个小店铺。后来父亲不辞而别,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我出让店铺,住进廉价的出租屋,大海捞针似的寻找我的父亲。我走遍这个城市的所有角落,眼睛里挤满老人们的身影,唯独没有父亲的脸庞。
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房屋,没有了店铺,我意志消沉。当我发现银行卡上的钱所剩不多时,不得不思索起了以后的生活,我才四十一岁,还有不少时光等待我去打发。我通过一个课外教育的中介公司找到一份家教的工作,我的第一个学生住在盛和路上,我与她的父亲通了电话,电话那端传来沙哑和迟疑的声音,说他女儿叫郑小敏,小学四年级,成绩很好。说他们夫妇两人都在工厂上班,收入不多,承担我每小时五十元的家教费有点困难。他声音里的无奈很像我的无奈,我说每小时三十元吧,他停顿一会儿后连着说了三声谢谢。
我们约好这天下午四点钟第一次上课。我去发廊理了头发,回家刮了胡子,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外面是一件棉大衣。我的棉大衣是旧的,里面的衣服也是旧的。
我走到熟悉的盛和路,知道前面什么地方有一家超市,什么地方有星巴克,什么地方有麦当劳,什么地方有肯德基,什么地方有一条服装街,什么地方有几家什么饭馆。
我走过这些地方,眼前突然陌生了,一片杂乱的废墟提醒我,盛和路上三幢陈旧的六层楼房没有了,我要去做家教的那户人家应该在中间这一幢里。
我前几天经过时还看见它们耸立在那里,阳台上晾着衣服,有几条白色的横幅悬挂在三幢楼房上,横幅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坚决抵制强拆”、“抗议暴力拆迁”、“誓死捍卫家园”。
我看着这片废墟,一些衣物在钢筋水泥里隐约可见,两辆铲车和两辆卡车停在旁边,还有一辆警车,有四个警察坐在暖和的车里面。
一个身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孤零零坐在一块水泥板上,断掉的钢筋在水泥板的两侧弯弯曲曲。书包依靠着她的膝盖,课本和作业本摊开在腿上,她低头写着什么。她早晨上学时走出自己的家,下午放学回来时她的家没有了。她没有看见自己的家,也没有看见自己的父母,她坐在废墟上等待父母回来,在寒风里哆嗦地写着作业。
我跨上全是钢筋水泥的废墟,身体摇晃着来到她的身旁,她抬起头看着我,她的脸蛋被寒风吹得通红。
我问她:“你不冷吗?”
“我冷。”她说。
我伸手指指不远处的肯德基,我说那里面暖和,可以去那里做作业。
她摇摇头说:“爸爸妈妈回来会找不到我的。”
她说完低下头,继续在自己双腿组成的桌子上做作业。我环顾废墟,不知道要去做家教的那户人家在什么位置。
我再次问她:“你知道郑小敏的家在哪里?”
“就在这里,”她指指自己坐着的地方说,“我就是郑小敏。”
我看到她惊讶的表情,告诉她我是约好了今天来给她做家教的。她点点头表示知道这件事,茫然地看看四周说:
“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
我说:“我明天再来吧。”
“明天我们不会在这里。”她提醒我,“你给我爸爸打电话,他知道我们明天在哪里。”
“好的,”我说,“我给他打电话。”
我步履困难地离开这堆破碎的钢筋水泥,听到她在后面说:“谢谢老师。”
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老师,我回头看看这个身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她坐在那里,让钢筋水泥的废墟也变得柔和了。
我走回到市政府前的广场,已经有两三千人聚集在那里,他们打出横幅,呼喊口号,这时像是在示威了。广场的四周全是警察和警车,警方已经封锁道路,禁止外面的人进入广场。我看见一个示威者站在市政府前的台阶上,他举着扩音器,对着广场上情绪激昂的示威人群反复喊叫着:
“安静!请安静……”
他喊叫了几分钟后,示威人群渐渐安静下来了。他左手举着扩音器,右手挥舞着说:
“我们是来要求公平正义的,我们是和平示威,我们不要做出过激行为,我们不能让他们抓到把柄。”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上午发生在盛和路的强拆事件,有一对夫妻被埋在废墟里,现在生死不明……”
一辆驶来的面包车停在我身旁,跳下七八个人,他们的上衣口袋鼓鼓囊囊,我看出来里面塞满了石子,他们走到封锁道路的警察前,从裤袋里掏出证件给警察看一下后就长驱直入。我看到他们先是大摇大摆地走过去,随后小跑起来,他们跑到市政府前的台阶上,开始喊叫了:
“砸了市政府……”
他们掏出口袋里的石子砸向市政府的门窗,我听到玻璃破碎的响声从远处传来。警察从四面八方涌进广场,驱散示威的人群。广场上乱成一团,示威者四下逃散,试图和警察对峙的被按倒在地。那七八个砸了市政府门窗的人一路小跑过来,他们向站在我前面的两个警察点点头后跳上面包车,面包车疾驶而去时,我看清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
晚上的时候,我坐在一家名叫谭家菜的饭馆里。这家饭馆价廉味美,我经常光顾,我的每次光顾只是吃一碗便宜的面条。我用饭馆收银台上面的电话给郑小敏父亲的手机打了几个电话,对方始终没有接听,只有嘟嘟的回铃音。
电视里正在报道下午发生的示威事件。电视里说少数人在市政府广场前聚众闹事,打砸市政府,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警方依法拘留了十九个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的人,事态已经平息。电视没有播放画面,只是一男一女两个新闻主播在说话。一段广告之后,电视里出现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西装革履的模样,他坐在沙发里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记者问一句,他答一句,两个人都是在重复刚才新闻主播说过的话。然后记者问他盛和路拆迁中是否有一对夫妻被埋在废墟里,他矢口否认,说完全是谣言,造谣者已被依法拘留。接下去这位新闻发言人历数市政府这几年来在民生建设方面的卓越成就。
坐在旁边桌子的一个正在喝酒的男子大声喊叫:“服务员,换台。”
一个服务员拿着摇控器走过来换台,新闻发言人没了,一场足球比赛占据了电视画面。
这个男子扭过头来对我说:“他们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我微微一笑,低头继续吃着面条。在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曾经搀扶他来过这里,我们坐在楼下的角落里,我点了父亲平时爱吃的菜,我父亲吃了几口后就吃不下去了,我劝说他再吃一点,他顺从地点点头,艰难地再吃几口,接着就呕吐了。我歉意地向服务员要了餐巾纸,将父亲留在桌子和地上的呕吐物擦干净,然后搀扶父亲离开,我对饭店的老板说:
“对不起。”
饭店老板轻轻摇摇头说:“没关系,欢迎下次再来。”
父亲不辞而别后,我一个人来到这里,还是坐在角落里,伤感地吃着面条。这位老板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询问我父亲的情况,他竟然记住了我们。那一次我情绪失控,讲述了我的身世,说父亲得了绝症后为了不拖累我,独自一人走了。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同情地看着我。
后来我每次来到这里,吃完一碗便宜的面条后,他都会送我一个果盘,坐下来和我说话。
这位老板名叫谭家鑫,夫妻两人和女儿女婿共同经营这家饭店,楼上是包间,楼下是散座。他们来自广东,他有时会对我感叹,他们一家人在这个城市里人生地不熟,没有关系网,生意很难做。我看到他的饭店里人来人往生意兴隆,以为他每天挣钱不少,可是他整日愁眉不展。有一次他对我说,公安的、消防的、卫生的、工商的、税务的时常来这里大吃大喝,吃完后不付钱,只是记在账上,到了年底的时候让一些民营公司来替他们结账。他说刚开始还好,百分之七八十的欠账还能结清,这几年经济不景气,很多公司倒闭了,来替他们结账的公司越来越少,他们还是照样来大吃大喝。他说,他的饭店看上去生意不错,其实已经入不敷出。他说,政府部门里的人谁都不敢得罪。
我吃完面条的时候,有人换台了,电视画面再次出现下午示威事件的报道。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在街上采访了几位行人,这几位行人都表示反对这种打砸市政府的暴力行为。然后一位教授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他是我曾经就读过的大学的法律系教授,他侃侃而谈,先是指责下午发生的暴力事件,此后说了一堆民众应该相信政府理解政府支持政府的话。
谭家菜的老板谭家鑫走过来送我一个果盘,他说:
“你有些日子没来了。”
我点点头。可能是我神色暗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坐下来和我说话,将果盘放下后转身离去。
我慢慢地吃着削成片状的水果,拿起一张当天的报纸,这是别人留在桌子上的。我随手翻了几页后,报纸上的一张大幅照片抓住了我的眼睛,这是一位仍然美丽的女人的半身像,她的眼睛在报纸上看着我,我在心里叫出她的名字——李青。
然后我看到报纸上的标题,这位名叫李青的女富豪昨天在家中的浴缸里割腕自杀。她卷入某位高官的腐败案,报纸上说她是这位高官的情妇,纪检人员前往她家,准备把她带走协助调查时,发现她自杀了。报纸上的文字黑压压地如同布满弹孔的墙壁堵住我的眼睛,我艰难地读着这些千疮百孔般的文字,有些字突然不认识了。
这时候饭店的厨房起火了,浓烟滚滚而出,在楼下吃饭的人发出了惊慌的叫声,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们一个个拔腿往外跑去。谭家鑫堵在门口,大声喊叫着要顾客先付钱,几个顾客推开他逃到外面。谭家鑫还在喊叫,他的妻子和女儿女婿跑过去堵在门口,还有几个服务员也过去堵在那里。顾客和他们推搡起来,好像还有叫骂声。我低下头继续读着那些黑压压的文字,饭店里声响越来越大,我再次抬起头,看到楼上包间里的人也在跑下来,谭家鑫一家人堵住门口,继续大声喊叫着要顾客付钱。没有人付钱,他们撞开谭家鑫一家人仓皇逃到街上。有几个顾客搬起椅子砸开窗户跳窗而逃,接下去饭店的服务员也一个个跳窗而逃了。
我没有在意饭店里乱糟糟的场景,继续读着报纸上的文章,只是不断地抬头看一看,后来是烟雾让我看不清报纸上的黑字,我揉起了眼睛,看着几个穿着工商制服或者是税务制服的人从楼上包间里跑下来,他们穿过一片狼藉的大厅,喝斥堵在门口的谭家鑫一家人,谭家鑫迟疑之后,给他们让出一条路,他们骂骂咧咧地逃到大街上。
谭家鑫一家人继续堵在门口,我看到谭家鑫的眼睛在烟雾里瞪着我,他好像在对我喊叫什么,随即是一声轰然巨响。
我来到了记忆之路的尽头,不管如何努力回想,在此之后没有任何情景,蛛丝马迹也没有。谭家鑫的眼睛瞪着我,以及随后的一声轰然巨响,这就是我能够寻找到的最后情景。
在这个最后的情景里,我的身心沦陷在这个名叫李青的女人的自杀里,她是我曾经的妻子,是我的一段美好又心酸的记忆。我的悲伤还来不及出发,就已经到站下车。
雪花还在飘落,浓雾还没散去,我仍然在行走。我在疲惫里越走越深,我想坐下来,然后就坐下了。我不知道是坐在椅子里,还是坐在石头上。我的身体摇摇晃晃坐在那里,像是超重的货船坐在波动的水面上。
一个双目失明的死者手里拿着一根拐杖,敲击着虚无缥缈的地面走过来,走到我跟前站住脚,自言自语说这里坐着一个人。我说是的,这里是坐着一个人。他问我去殡仪馆怎么走?我问他有没有预约号。他拿出一张纸条给我看,上面印有A52。我说他可能走错方向了,应该转身往回走。他问我纸条上写着什么,我说是A52。他问是什么意思,我说到了殡仪馆要叫号的,你的号是A52。他点点头转身走去,拐杖敲击着没有回声的地面远去之后,我怀疑给这个双目失明的死者指错了方向,因为我自己正在迷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