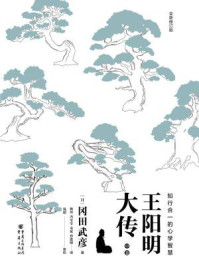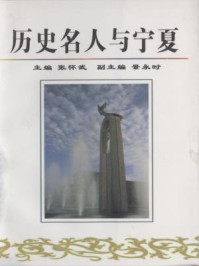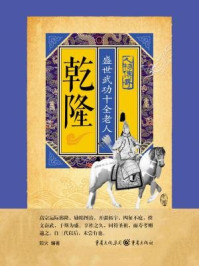群山中间有一座城。它那些古旧的楼阁被夕阳映成了金红。蜿蜒交错的街巷凌乱得像一所花园的曲径,全被深锁在厚的城墙内,墙上耸立着一些坚固的城楼。每道街,每条巷,仿佛都隐藏着它特殊的秘密,一个陌生的人要想了解它,是不会成功的。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在那些尖屋顶的老宅的阴影中存在着久已被人遗忘了的古昔的往事。
市场上古老的喷泉像往昔一样地在柔声低语。古寺院的巨影躺在寂静的广场上,这广场在今天显得十分荒凉。只有一个憔悴的老妇孤寂地站在古喷泉旁边,梦想着那些永不会再来的逝去的时日。
春天突然来临,漫长的冬日的暴政一下就给终止了。灿烂的晴空和牧场、草地的新绿引诱人们走出到郊外来,欢乐的人群在明媚温暖的春光里无拘束地跳荡、漫游,他们的久被麻木封锁了的心得到解放了,春天的太阳使这麻木融化消散了。今天成群的人,不论年幼老少,全走到露天里来,抖去他们灵魂上的尘垢,并且证明严冬的阴郁单调并没有损害他们丝毫。
现在已是傍晚,古老的钟声庄严地响彻了和暖的空气,警告城里人说,这是回家的时候了。快乐的人群像水流似的穿过城门,他们带了成束的鲜花和草木回去,欢快的歌声充满空中。古老的街道挤满了笑谈着的人们,他们安闲地、喜洋洋地走回家去,最后街巷中、广场上人影和语声跟着逐渐加浓的夜色慢慢消失了。
落日的最后光线早已褪尽,柔和的春夜静悄悄地罩在荒凉的街巷的上空,这些静寂的街巷在月光里奇异地闪烁着。
小窗中灯光渐次灭了。只有三两人家的孤寂灯光点缀了静夜。也许是一个病人正躺在那儿同痛苦挣扎,再不然有一个垂死者正把他疲乏的灵魂托付给上帝。
深沉、庄严的和平笼罩在这些沉睡的房屋的上空,偶尔有古寺院的庄严的钟声和守夜人的轻快的号角打破了这静寂。
在这沉睡的古城的中心一个小丘上,耸立着一所年代久远的堂皇的建筑物,它比四周的房屋更奇特,更古老。在一间塔里的屋子的尖拱式小窗前坐着一个白发长髯的老人,他正呆呆地望着窗外,他的眼睛越过那些在淡白色月光中发绿光的古屋的尖顶,凝望着远方。

浮士德
屋子正中有一张笨重的橡木桌,桌上凌乱地堆满了书籍和文件。顺着褪色的墙壁放了些长架,架上陈列着珍奇的标本和古怪的仪器。一盏精巧的油灯放射出微光,它想照彻这屋子的幽暗角落,却没有用。
老人带着倦容把覆在前额的长发往后一抹,沉思地喃喃自语:
“现在一切又像坟墓似的静寂了,在沉睡者的头上仍旧拱立着那无限空间的穹窿,在那里数百万个世界继续不停地沿着它们的轨道转动。但愿他们的睡眠得到提神的效果,不被噩梦惊扰!谁能够做到这样呢?只有那些始终注意着目前的一点点需要、从不想建造通到永恒去的桥梁的人。愿他们有福!造物主并没有给他们一种过事强求的性格。要扰乱他们的平衡是很难的。因此他们居然能够免掉受一种欲求的煎熬,在有些人这折磨人的欲求正像一只饥饿的虫咬着他们的心。
“我觉得这欲求像一种慢性的毒药留在我的血里,这时候深不可测的大自然正辗转在‘再生’的痛苦中,新的生命从无数的喷泉里迸出,它们的样式永远是新的。春天慢慢地过去了,夏天和秋天也渐次消逝,严寒的冬季又来把万物都包在它的尸衣里面。于是那个老戏法又开始了。谁能够探知这种永久的成与逝的奥妙呢?在这里面生与死是这么奇怪地混在一起,而每个终局又正孕育着一个新的开端!
“在那广大的事实的循环中,死究竟是一个终局,或者只是一个开端,抑或同时是终局和开端呢?分隔‘过去’与‘未来’的界限又在什么地方?并且一切生物从那儿出来的那个缥缈无边的造物主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我越是研究这个难解的谜,我越是觉得自己不了解自己。我对自己的天性感到了一种神秘的畏惧,我自己的天性在我眼前就跟无限空间本身的沉默无言的永恒一样地深奥难解。
“我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难道在我母亲身体怀孕一个新的生命之前我就存在着吗?难道在我这个生存的最后一星火花像火烬那样地灭了以后我还继续存在吗?
“我们有着很多阴暗、神秘的东西,深藏在我们的灵魂里,永远不出现到表面上来给人看见。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琐细挂虑和我们所极难得有的小小欢乐这两样,我们所能彼此相告的也只是些表面的事情,它们影响我们的程度也不比那些无意识的机械动作高多少。然而那些沉睡在深处的东西并不想露面,它们睡在心底,在那儿不为人知的原始力量默默地往复循环,从来不走出到光天化日之下来。
“在燃烧着的性的烈火的中间,颤抖的身体紧紧相偎着,两个灵魂似乎溶化在激情的疯狂的骚动里,甚至在这个地方,也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它静静地隐伏在感情的后面,所以总有一些话不会吐出,总有一些极深的欲念不会平息。甚至在爱情带着陶醉酣睡的地方,也有一个带威胁性的谜样的东西,始终在思想的深处闪烁。谁知道呢?
“是的,要是我们真可以去参观造物主在他的工场里工作的情形,把一切事物的开端和终局看个明白,那么我们或许也会知道在围绕着我们脑筋的那道薄墙(许多隐秘的思想都拥挤在它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并且暗暗地藏在不会给人发见的地方)的另一边躲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那时候生命的意义对我们便不再是一本密封的书了。然而我们的一切的探索又有什么用!我们这些渺小的可怜人,凭我们的思想不过紧紧抓住事实的表面,而且每逢我们以为我们找着解答,得到领悟的时候,我们总是最愚昧、最不明白的。
“在这许多烦闷不安的夜晚,我坐在寂寞凄凉的屋子里。我的贫弱的脑筋反复地思索着会把我从永久的苦痛中拯救出来的那些包容世界的广大思想——
“拯救吗?仁慈的圣处女啊,您是纯洁的,尊贵的,您这个住在天堂里上帝圣座旁边的女人!从您那神圣的身体中生出了基督,他把人们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可是拯救我的救世主却好像并没有出世;因为没有一个救助者曾经熄灭过我胸中那股热切的渴望的烈火。
“啊,要把人从他的各种小的罪孽中救拔出来倒还容易,可是要给他解除那些一直在深不可测的深渊上面盘旋的纷乱思想(那些不断地在要求着理解的思想),却困难了!这个大的渴望,它一直在期待着一个启示,并且在隐沉的痛苦中不自觉地咬蚀自己,它真有得到解救的时候吗?
“追求我一切热望的实现的念头曾经像一颗明星似的在我的头脑中萦绕过,可是随着岁月的重荷的逐渐加重,它也越来越远地逃到远方去了,只剩下一些无用的残屑。
“当我的身体里还充满着青春的力量,而我还用清晰的目光正视生活的时候,我曾经梦想过那一个崇高的时刻:那时命运用来束缚我的结子都在我的手里解开了。我的心带着热切的冲动抓住了人智所产生的一切,并且在古书中,在古昔的制度中寻求智慧的终极目的。可是每次那渴求看见它前面有了一道门,心灵在地平线上瞥见了它的终极目的时,事实上那却只是另一个开端,难理解的,就像一星在坟墓上空嘲弄地跳舞的鬼火。
“在岁月默默流转的过程中我确定地知道了一桩事情:我们的全部知识并不帮助我们理解事物的终极的意义。我们好像盲人似的永远在绕着圈子。我们向着一个遥远的目标走去,但我们总是回到同一个老地方来。
“在那包容一切的永恒的空间中有无数的世界在非常奇妙地旋转运行,在这些世界里面,除了我们居住的地球外,是不是别一个的上面也有人一类的生物,他们也像地球上的人一样,在追求着理解,并且顺从着那个热狂的欲求,也会在地狱的痛苦和天堂的幸福中烧毁着自己?
“我常常觉得我听到从极远极远的地方传来那通入无穷的深处的世界的无声的节奏。它像一声强大的弦音落进我的灵魂:我以为我听见了天体的和音,于是整个生存的理由就突然变成很明白的了。然而等到我动一只手用文字去缚住我那内心的经验时,这短暂的魔力立刻就像一个气泡似的破散了;我身边只有寂寞空虚。
“然而那个靠我的心血养活的大的渴求,那个一直在追求理解的热情的渴望,它从不离开我;虽然我始终在各种失望中间绕着圈子走不出来,它也从不离开我。甚至在今天,墓门已经为我这个‘衰老’的身体开了一个缝隙,我那个大的渴求也不会静止。并且这隐秘的痛苦似乎变得更厉害了。为什么,呵,为什么呢?
“我一直是极虔诚的!我永远是一个传播您的光荣的不偏不倚的使者!
这时房中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发出来一阵快乐的哄笑,一个声音说着:
“你这傻子!你这老傻子!你那老朽的肢体已经感到了死亡的冷冰冰的抚摸,然而你还不能够制止你的疯狂。难道你从没有认清你自己最深的天性?你一生都在幻想你自己是个虔诚的人,可是你就从没有虔诚过。你知道真正的虔诚是什么吗?一个人的虔诚是从他的内在的冲动来的,他完全服从神的命令。他不计较,不隐讳,他更不会被那些狡猾地潜伏在心底、切望着实现的隐秘欲望所煎熬。
“在你,虔诚只是一个达到特殊目标的工具。你赞颂你那造物主的光荣,忠实地遵守他赐给你的诫命,可是在你的内心却深藏着一个妄想:你以为将来有一天你会得到理解作为报酬,上帝会拉开你眼前的网幕,让你明白他的工作的意义。
“老头儿,这是空的希望!你在让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梦愚弄你自己。你的眼光定在一个幻影上面,那幻影闪出千种颜色的灿烂的光,却只是欺骗地引诱你离开正路,更深地走入沙漠中去。
“你的上帝就像一个回教徒那样地妒忌;的神性也会全完了。
“因此便蒙蔽着人的心,拿一个终极目标去跟人的渴望开玩笑,这目标是人达不到的,人越是想追上它,它越是退得远。这样,人好像古寓言中的那个生物,它的热切的眼睛总是看见前面悬垂着新鲜的果子,可是它的嘴唇始终挨不到它。几千年来人一直是给缚在牵孩带上,然而他从没有注意到他给欺骗得多惨!
“老头儿,你走错路了!倘使你想求得知识,你应当敲我的门——”
声音停止了,房间里响起来一阵轻微的衣裳的声音。
老人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谁在跟我讲话?”
从一个角落里发出来刺耳的尖声:
“谁在跟你讲话?人称我为‘黑暗之力’,因为我从天上偷了火给地之子们带来光明。人曾经称我作‘说谎的王子’,因为我第一个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真话。
“那个谦虚的词儿‘为什么’就是从我的心中想出来的。从前你的祖先们跨出了那道分隔人兽的门槛时,我就用这个词儿去迎接过他们。这个词儿钻进了他们的愚钝的脑筋,像一个重物似的沉落到他们的心底去了。
“无穷无尽的人群在所谓罪孽的诅咒之下跪倒在尘埃里礼拜上千位的神,一面损毁他们自己的身体,一面痛苦地呻吟。我亲眼看见他们心灵的苦痛,我只问着一个词儿:为什么?
“那班做奴隶的人流血汗做牛马建造了金字塔和卫城,这些伟大的建筑物会把他们主人的名字留传到无数的世代。我望着那班奴隶的疯狂,我只问他们:‘为什么?’
“然而这个藏在他们心底的词儿有时候也会突然发出亮红的火焰。于是魔鬼依附在他们的身上。神们从的圣殿中逃了出来,宝座也给丢在阴沟里了,那些铸造来作永久用的链子也断了。然而这情形并没有继续多久。他们的血液里还保存着对鞭子的爱好,他们的肩头又在渴求着一个新轭了。
“谁在跟你讲话?我就是那个在天堂中出现在你母亲面前的魔鬼,我求过她伸出手去摘知识树上的果子。我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过:上帝知道你吃掉那个果子以后你的眼睛就会给扳开了,你就会跟神们一样,知道善恶。
“上帝把你的父母像狗似的从天堂里赶了出来,又诅咒大地教它不得养活他们,并且把他们交给奴役和死亡去支配,这并不是我的错!
声音又静止了。老人的疲乏的身体上起了一股战栗,从他的嘴唇中发出来沉滞的声音:
“撒旦,是你在跟我讲话。你要把我引入魔道,骗我去受天罚吗?你的论理的锋利使我恐惧!然而我整个身心都在呼唤你。你不答应给我知识和理解吗?我的旧创口开始在流血;我的心又受着那些折磨人的问题的煎熬;那些我以为已经埋葬了的欲望又从我的灵魂的深处挣扎着出来了。它们像烈火似的烧着我,我的灵魂忍受着它们的那无数的苦刑。难道我的渴求得着满足的时候终于到了吗?
“然而人说魔鬼是不可信赖的。他从没有单是由于好意做过一件事。那么请你明白地、坦白地告诉我:你做这件事情,期望着什么报酬?”
从角落里送出来回答:
“很小,几乎不值得提说。
“只要你活着一天,你任何的愿望都可以实现。不管你的幻想想出什么,不管你的心想望什么,我都不会使你失望。时间与空间,死亡与永恒都会显得像水晶那样地透明,每个谜的难解的结都解开了。你也会了解整个存在的理由和一切事情的想得很周到的计划。直到这时为止你的心都不能越过的最后的界线也会在你的眼前消失了。连你那最小的一时的怪想也会是我的法律,要是什么时候我对你失了信,那么们中间的关系就中断了。
“然而将来有一天你的最后的时刻来了,你的活力已经消耗净尽,你的精神要准备长眠了:那以后的事就得由我来决定。你便无权过问了。
古老的木板发出轻微的响声,淡淡的影子在颤摇的灯光的四周晃动。天堂与地狱正在这倦怠的灵魂中追逐着互争胜利。于是这老人的眼中射出来强烈的光,他用坚定的声音说话:
“好吧:我要接受你的条件。要知道!要理解!就是一会儿也好!要看透事情的旋涡,要看见整个存在的根底,这是我渴想了多年的了。我简直不能够相信:我想望了多年的时刻到了,它给我带了拯救来。然而我始终认为那个为了大多数人死去的救世主绝不能够拯救我。
“只要我的心渴求着理解而无法得到满足,我的灵魂受着欲望的折磨的时候,我还管什么死亡与复活,地狱,时间和永恒呢!这种未满足的冲动咬蚀我的心不是比地狱的痛苦还厉害吗?所以我认为与其整日整年在闭着的门前徘徊始终不能够看到谜底,还不如把这确实的痛苦永久担在自己的肩上。
“撒旦,我准备好了!只要能够看到‘无穷’的奥妙,就是短短的一瞥也抵得上一切地狱的痛苦!
从屋子的阴暗处走出一个瘦长的人,帽子上插一支公鸡毛,身上穿一件红色大氅,他大步走到灯光照亮的圈子里来。他那苍白的瘦削的面貌好像是用一柄凿子刻出来似的,他的嘴唇边流露出傲慢的嘲笑。他用尖声说:
“好,老头儿!你倒讨我喜欢。不过我早就知道有一天你要来找我。那个圈子对你并不相宜。一个人心里藏得有那么深的奥妙,是不适宜于信奉上帝并且遵守上帝意旨的。
“不过现在,你且起来,走出这些窄狭的墙壁吧!住在一所正在腐朽的房屋里面,你的心也在霉烂了。要是你想了解生命的最深的意义,你得到各处去旅行,你不能把你的灵魂加上镣铐锁在满是尘土的窗后和发黄的羊皮纸书页上面。外面在那一边还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在笑着,它会使你那不宁静的精神得到它所渴望的和平。
“然而在我们离开这间屋子(对你它可以说是一间拷问室)以前,你得改变你的外形。年龄是人必须负担的最重的担子。在一个衰老的身体中连心也变老了。真理刚刚在一个衰老的脑筋里略为成形,它就已经开始在内部腐朽了;它还没有出世,就受到虫蚀和死亡的威胁了。
“把这个粉拿去;放在水里溶化,然后用水洗你的头和四肢。你很快地就会感到它的效力。”
老人照着吩咐做去,用不老药洗他的枯萎的身体;他简直不能相信在他身上突然发生的奇迹。时光在他额上刻下的皱纹被魔力抹去了。白胡子没有了,刚才还盖满他头顶的白发也不见了,还有那常常使他记着他的末日就要到来的衰老病也跟着消失了。
一个年青人站在窗前,长着满头的金发,身体非常结实。他的眼里露着年青的活力。青春春像火似的流遍他的四肢,神秘的力量使他的神经强健。对于他,现在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他觉得生命的脉搏在他的血管里跳着。他的胸膛里充满了巨大的力量。
他的热烈的眼光尽量吸收他四周的光辉;在他耳边响着的每个声音,都像少女的接吻似的使他的心颤动。
两个人跨出了老屋的朽烂的门槛,沉重的门带着响声在他们的背后关上的时候,曙光开始在东方露面了。他们迈着轻快的步子急急走过那些尚在睡梦中的静寂的街道,到了古老的城门前。年老的守门人带着睡意给他们打开一道窄门,放他们出去。
那城市现在是在他们的后面了,他们勇气十足地大步走上一座小山,从山顶一望,远近的景物都华丽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年青人用陶醉的眼光望着下面的山谷,他那瘦长的同伴脸上却露出淡漠和厌烦的表情。
树林和田野沐浴在朝日的灿烂光辉里。云雀颤声歌唱着,飞向天空,高声地欢迎那大而发光的日轮。围篱边和灌木丛中送出来快乐的鸟声。蝴蝶栖息在带露的花朵上,布谷鸟在附近树丛中发出引诱的唤声。一条小溪在山谷里淙淙地流过,在那一边躺着古城,罩上了一层薄雾:那是一个受了睡眠的魔力的世界。
自然界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在他眼前显得非常可爱。他从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到他自身跟一切生物的和谐。多年来压在他的灵魂上面的重物已经消失了,他的精神在澄蓝的太空浮游,就像一只船在平静的湖上一样。
这两个飘游者闲适地从山的另一边走下去,进了山谷,沿着蜿蜒流向远方的小溪闲步,走到了一道小桥的桥头。
一个少女闲适地站在对岸,她穿了一身细料子衣服,她的金丝发间插着鲜花,她不过十七八岁的光景;她那对清澄的眼睛坦白地、天真地望着这两个浪游者。年青人贪婪地捉住那一对多情的眼里射出的动人的目光,一种他从来不知道的感情温柔地抓住了他那悸动的心。
这会是爱情吗?他以前从没有了解过爱情是什么。在他看来爱情只是那班一生中没有正当目标的坏人的小罪过。他以为女人是无谓的快乐和罪孽的缩影,它把男人从义务与严肃思想的路上拉开,浪费他的力量,使他过着无目标的生活。
因为这个缘故他便不许异性走近他的住处,免得邪恶的欲望扰乱他的生活圈子,剪掉他的灵魂的翅膀。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跨过他那间屋子的门槛,他在那屋子里度过了他的大半生,陪伴他的只有那些骚动的思想,它们躲在这屋子的每个角落里,就像是一些从未知的世界里来的胆小的送信人。那里从来没有过逸乐和色欲的事。
然而现在这个少女的目光射进他的心里、在那儿燃烧的时候,他起了一种新的感情,这感情恰恰适合他那种自身与他四周的一切相和谐的心境。求爱的冲动,对这个不认识的异性生物的渴望,健康地在他全身中流动,使他的灵魂里充满了热情。他的脚步放慢了。他困惑地偷偷看了看他身边那个瘦长的同伴,那个同伴这些时候一直带了含有恶意的眼光望着他,慢吞吞地对他说:
“这个美人儿打动了你的心。她的确是一个整洁的小东西!她还是像露一样地新鲜,很合胃口。不要制止你的感情。不要放过现在你可以得到的东西!我的高贵的年青人,只管朝前走!不要害羞!她不会拒绝的,那个小东西。我正要走开一忽儿;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来服务的。”
年青人用坚决的脚步急急走过了桥,他那爱抚的眼光拥抱着少女的美丽的身体。他那些赞美的话语诱惑地在她的耳边倾吐。她含羞地垂下眼睛,一层红晕上了她的面颜。随后他们两人就坐在老榆树下一块长满青苔的大石上像知己似的亲密地谈着。后来他们的手握在一起,嘴唇因接吻而静默了。
这一对年青人默默地站起来,他们仍然紧紧地偎抱在一块儿,慢慢地朝着近旁的树林走去。那个抄着手站在对岸的同伴,一直用带恶意的目光望着他们,他轻蔑地在一边说:
“人啊,你这可怜的精神和泥土混合做成的东西!精神一直想把他抬到天上去,可是泥土却总是在拉他下地来,所以他一直在爬着,一直在追求。人真是一个古怪的东西!他老是在寻求‘点金石’,然而等他觉得知识就近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却做出他一生最大的傻事来。他的心在探求着天空,梦想着星星,可是他不明白他正像一个喝饱了新酒的醉汉似的,躺在阴沟里面。
“七十年来,他一直坐在那边他那所房屋里,梦想着建造一道通到‘无穷’去的桥梁,把他一生的精力完全消耗在他自己造出来的苦刑里面,他实在应该发狂了,因为他的上帝不肯拿开他眼睛上的缚带,让他看清楚一切谜的谜底。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绕行世界的思想,他常常幻想自己听见遥远世界的节奏。他带着热切的眼光等待黑暗帷幔的揭开,让他看见生存的目的和意义。等到他渐渐地明白他所有的努力都受着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他的心智绝不能了解事物的理由时,他完全灰心了,他的灵魂在说不出的痛苦中向求救了。
“可是今天这个傻瓜已经治好了。现在他尝到了血,他那大渴望会渐渐地淡下去了。他那个从前极勇敢地想攀登世界最高峰的灵魂也会以维纳斯山
 为满足了。他不再渴求理解一切事物后面的奥秘,他要知道一个女人围裙后面的秘密了。这个学问会使他更快乐,而那个他花去一生时间所建造但始终不能给它一个定型的空中楼阁般的思想跟这个比起来却差得多了。因此那个未满足的渴求和那些最后的希望在不知足的欲火的面前也会消失了,而那可以达到的欲望也会使求知欲大大地减弱。
为满足了。他不再渴求理解一切事物后面的奥秘,他要知道一个女人围裙后面的秘密了。这个学问会使他更快乐,而那个他花去一生时间所建造但始终不能给它一个定型的空中楼阁般的思想跟这个比起来却差得多了。因此那个未满足的渴求和那些最后的希望在不知足的欲火的面前也会消失了,而那可以达到的欲望也会使求知欲大大地减弱。
“然而他永不会了解他干的傻事的性质。因为就是对一些小事物他的眼光也只是集中在远的上面,而近在他鼻端的他却反而看不见了。他夸耀他的自由意志,相信他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傀儡,由一些暧昧不明的力量牵着线叫他跳舞。
“现在他恨他的上帝,因为上帝愚弄了他,这许多年来上帝一直把他拴在牵孩带上,不给他自由;他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已经吞下了一个新的饵,他又吊在一个钩子上了。自然他想不到,是他自己放出的饵,做好的钓钩,而他又跟别的人一样把饵吞下了。
“然而这个真理就在他的近旁。我跟上面那儿我那些弟兄还不是他的神秘的需求的创造物吗?他的精神创造了我们,信仰的热情产生了我们,把我们丢进了现实的国土里。
“所以永远重复着同样的牌局,并且结果总是一个僵局,因为双方的牌总是相等的。不管是上帝或撒旦最后拿到较大的王牌,机会还是均等的,结果并无分别,因为总是拿人来作赌注。”
岁月在时间的花样繁多的戏法中间飞逝了,这两个浪游人不休息地赶他们的路,走遍了陌生的国土,飘过了陌生的海洋。那个瘦长的人玩了不少聪明的把戏。每一次他施他的魔术时,观众都伸着颈子和手膀,或者在胸上划着十字,畏怯地躲开了他。
他十分了解生活的盛衰苦乐,他跟学生、农人、旅行者都处得很好;连达官贵人的显赫声势他也极其熟习。在好些宫廷里他都是受欢迎的客人,他施魔法从国王们的金库里弄走他们的金钱,一面却用戏法和幻术欺骗他们。
然而对这瘦长人,这并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因为那个靠了他的魔术而得返老还童的人的古怪想法太多了,多得像海中的沙一样。他的脑子里装满了上千的欲念和欲望,而每一个愿望又立刻生出一大串的愿望来。在飘浮不定的思想的这种杂乱中,没有一个休止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固定点。这些思想发狂似的旋转追逐,它们还没有由他顺着思路想到底,就已经死了。这是情感的不断的起落,这是那些无目的无方向而永不休止的激情的一场大火。
许多年以前在他的心里燃烧的东西,那个追求事物的理由的切望,那个追求理解的渴求,早已死亡而且被埋葬了。只有偶尔在人静的时候,一个轻微的声音使他记起了已经逝去的时代。于是从前那个老的渴望又突然涌上来了,他的精神战栗地听到了遥远世界的轻微声音。然而那个瘦长的人连忙用戏法和谈话把他从他的梦中抓出来。他的心灵只得匆匆离开,走上新的路去,而他一切的渴求又痛苦地消失在心底了。
这样的岁月一年复一年地堆积起来,老年第二次缓缓地来了。他的头发发白,眼光模糊,在他的内心又张开了空虚的大口。
现在瘦长人常常让他安静,更少来打扰他的沉思了。一种大的寂寞抓住了他的纷扰的心,人生的路在他的眼前显得凄凉乏味了。
秋天拖着疲乏的脚步在外面走过,树叶无声地从枝上落下来。枯叶在风中打旋,伟大的死亡走过了田野和树林。在他的内部,秋天也已经慢慢地来了;只有在他的心底还燃着一星从前煎熬过他、把他从故乡赶到异域去的烈火。
今天他跟从前一样,又坐在家中了,他反复思索着那些忧郁沉闷的思想。秋风猛烈地吹过夜空,像责斥似的摇撼着他这所老屋。他像许多年以前那样坐在窗前,疲乏地望着外面阴暗凄凉的空间。然而今天外面并没有一颗远方的星为他闪耀,也没有一线月光穿过黑暗了。在他的头上天空张开着像深渊一般的漆黑大口。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坐在一个井里面,有一些黑影正从很深的井底升起。他喃喃地说:
“现在这赌局快完了。那个瘦长的、鬼鬼祟祟的流氓好像已经溜走了。恰恰在今天他得向我交账的时候,他却卑鄙地逃走了,把我丢在困难的处境里面。其实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为我做什么呢?他的存在快叫我不能够再忍受下去了。事实上我以前一直是孤独的,就是跟别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是这样。今天我更需要孤独,免得在我一生最后的时刻里,还有嘲笑来扰乱我的心。”
现在他充满了和平的梦景的回忆。一个低音的调子从心的深处响了起来。难道这是他很久、很久以前偶尔听见过的遥远世界的节奏,好像永恒的轻微声音似的遥远世界的节奏吗?
一阵凉风吹拂着他的燃烧的额头,思想敏速地从他的心底涌上来。在他的脑子里思想毫不费力地转成了语言,这些思想现在是水晶似的透明了。他从没有把事物看得这么深透过。他畏怯地问他自己:
“难道这是最后的启示吗?就是在终局到来之前的最后的启示吗?好像那些遮蔽我的视线的尘垢都从我的眼睛上落下来了;最后的幻想也破碎了。我第二次给人出卖了!在我受骗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是多么地强壮!
“牧童一生也只能被人愚弄一次。然而我这个被全世界所称为大贤的人却让人戏弄了两次了。
“最先是上帝一直用牵孩带拴住我,随后是撒旦来教我怎样行为。而我,我真蠢,我没有能认出这个可耻的把戏,在我不过做着他的意志的傀儡和受他欺骗的瞎了眼睛的傻瓜时,我还觉得自己是个主人!
“当我奋然扯掉那根一直把我拴在上帝身边的带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多么伟大,多么像一个造物主!我要探究窥测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我因此牺牲了我灵魂的幸福,甘愿为一个时间极短的理解永受天罚。
“撒旦允许我这个。而我,我这傻瓜,我相信了他的话,我像蠢物似的完全服从他的命令,就从没有想到我不过是一个受着他的怪想支配的玩具。
“他答应给我理解。然而他并不给我知道生命的意义,知道一切事物的开端和终局,他却给我女人,引诱我拿平凡的调笑来消遣。煽旺了我的情焰,麻醉了我的心智。我还来不及猜出他的目的,他已经把我的灵魂改铸成小钱币,并且剪去我的渴望的翅膀了。
“然而现在谜的核心已经显露给我看了:上帝和撒旦是同一个种族的,是我们生命所绕着旋转的两极。没有上帝就没有撒旦,没有撒旦就没有上帝!他们是在同一个时刻生出的一对双生子,他们生下来就带着同一个轭,这轭把他们永远拴在一块儿一直到最后。
“人就在这个圈子里生活。我们永远从一个极趋向另一个极,可是始终逃不出那个用魔法把我们拘束住的圈子,要是有一天我们居然明白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在愚弄我们,我们就立刻转向了另一个,在需要的时刻向他求助,把他当作救主。
“这时他已经在等着我们了,他交给我们那同样的料子,不过却印上了一个新花样,使我们认不出是旧货。上帝和魔鬼就是这个老店的名字。两个合股的老板中间缺不了一个;否则生意就没有了。
“只要我们的心灵一直在这个圈子里绕行的时候,它是永远受不到理解之光的。因为理解(我清清楚楚地这样觉得)是在上帝与撒旦的圈子的外面;而且远得没有路通到它。
“在我现在是太迟了;我觉得我的时刻已经到了。我的疲乏的四肢渴求着休息。然而我的种族不会跟我一块儿死去。只要人还活在地球上的时候,他的心会一直去追求理解的:一直到他的子孙在时间之流中灭亡为止。
“现在‘未来’清清楚楚地横在我的眼前。我的耳朵听到一个类似遥远的风琴乐曲的声音。这是下几代人的赞美歌:
“在东方远远地,远远地射出来另一个太阳的光芒,这太阳从没有照过我们的地球!然而现在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刻逼近了。我已经可以看见沙漠的暗黑的边缘了。
天灰暗。平沙无垠。
一个光黑的云母石大斯芬克司躺在褐色细沙上,她的眼光注视着荒凉的、没有尽头的远方。
这眼光里没有恨,也没有爱;她的眼睛是朦胧的,仿佛给幽梦罩上了一道纱似的,她那冷傲的、缄默的嘴唇微露笑容,微笑中带着永久的沉默。
第一个浪游人走近了,他看入斯芬克司的眼睛,然而他绝不能够解答她的谜;他默默地倒下来,睡在沙漠的细沙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