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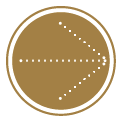 高额奖金是一柄双刃剑
高额奖金是一柄双刃剑
我们认为,高额奖金对成绩的负面作用肯定有限—不管怎么说,高额奖金似乎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降低成绩。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有一种限制因素(心理学家称为“调节因素”)会根据工作所需的脑力劳动的程度不同而发挥作用。对于认知能力要求越高的工作,我们认为,高额奖金产生反作用的可能性越大;而对于非认知乃至机械性的工作,奖金越高可能成绩就越高。例如,你蹦跳一下我就给你多少钱,让你 24 个小时不停地跳会怎么样?你是不是会尽最大力量来跳,而且给钱越多跳的时间越长?如果奖金非常高而你还有力气,你会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不跳吗?这不可能。对于从事很简单的机械性工作的人来说,我们很难想象高额奖金会产生反作用。
我们的实验项目包括了差别很大的各种游戏,令我们惊讶的是,所有游戏里奖金最高的一组成绩最差,和我们的上述推理完全一致。我们原以为认知性较强的游戏,例如赛门和复述最后 3 个数字会和我们猜测的一样,而没有预料到像飞球和爬坡这样机械性的游戏也不例外。这是怎么回事?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对于机械性工作的直觉是错误的,即使对这一类工作来说,高额奖金也会降低成绩。另一种可能是,我们所认为的认知要求较低的游戏(飞球和爬坡)仍然需要某些脑力因素,我们需要在实验中引入纯粹机械性的游戏。
考虑到这一问题,我们下一步把实验分成两种情况进行对比,一种需要认知能力(简单的数学题运算),另一种只需要简单操作(快速敲击键盘上的两个键)。我们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中进行实验,检验纯粹机械劳动中奖金与成绩的关系,与脑力工作中的情形相对照。限于我们的项目预算,我们无法给出与印度实验时相对应的那么高的奖金。我们只能等到学期快结束,学生们的钱包都瘪了的时候再说。这时,大约 20 分钟的任务我们给出 660 美元的奖金—这钱足够他们举办几次派对了。
我们把实验设计成 4 个部分,每个参与者必须全部参加(这种安排被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做“被试内实验设计”)。我们要求学生们完成两次认知任务(简单的数学解题):有一次给出较低奖金,另一次给出较高奖金。另外还要他们进行两次机械性操作(敲击键盘):一次较低奖金,一次较高奖金。
这个试验向我们说明了什么?不出所料,我们发现较高激励对两类不同工作产生的作用不同。如果手头的工作仅仅是敲击键盘,奖金越高成绩也越高。但是,一旦工作需要基本的认知能力(计算简单数学题),高额奖金会对成绩造成负面效果,就和我们在印度实验中看到的一样。
结论很清楚。发放高额奖金对简单的机械操作类工作可以提高业绩,如果需要人们动脑子则可能适得其反—而企业通常向从事脑力工作的高管发放巨额奖金。如果高级副总裁的任务是砌砖,用高额奖金激励他们情有可原。如果他们的激励基础是奖金,从事的是筹划兼并和收购,或者创造五花八门的金融工具的工作,奖金的效用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差很多—甚至可能带来负面效果。
总而言之,金钱对人的激励可能成为双刃剑。需要认知能力的工作,业绩与较低或中等数额的奖金挂钩会起作用。如果奖金金额太高,会使人过度关注奖励,从而分散他们的精力,造成压力,到头来反而可能降低他们的业绩。
谈到这里,理性经济学家可能会争辩说实验的结果对企业管理人员并不适用。他可能这样说:“不过,在现实世界上,薪酬过高的问题绝对不存在,雇主和董事会都会把业绩下降问题考虑到,他们不会采取无效的激励措施。”“说到底,”理性经济学家会坚持认为,“雇主是完全理性的,他们很清楚什么样的激励方式能提高雇员的业绩,什么方式不能。”

他这样说非常有道理。不错,人们可能对高额奖金的负面作用有直接认识,因此绝对不会有意发放过高奖金。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多数人所具有的其他非理性本质一样,我们可能不了解各种力量,包括奖金如何影响我们。
为了检验并找出人们对于高额奖金的直觉,我们把在印度实施的实验向斯坦福大学的一大批工商管理研究生作了详细介绍,并要求他们对较低、中等以及非常高的奖金条件下人们的成绩进行预测。因为我们没有告诉这些研究生实验结果,这些“事后预言家”(事情发生后作预测)预测的成绩与奖金水平同步提高,他们这种预测对于较低和中等奖金的激励作用是正确的。但是到了预测高额奖金的效果时,他们的结论就南辕北辙了,他们全都认为高额奖金一定会导致更好的成绩。
学生们的回答表明,高额奖金的负面效应仅凭人们的直觉是不会自然而然地被认识到的。它还表明薪酬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严格验证,不能仅仅依赖直觉推理。不过,企业和董事会能摈弃自己的直觉而采用验证过的数据来决定工资吗?我怀疑。事实上,每当我有机会向企业高管陈述我们的实验成果时,我都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对现行薪酬制度的功效知之甚少,而且对如何了解和改进丝毫不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