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普通德国人,1945—1955
- 理想国 | 哈拉尔德·耶纳
- 24.8万字
- 历史

内容简介:战后的德国,一个充满占领者、被释放者、流离失所者、被疏散者、逃亡者以及背负着战争罪行的人。他们掠夺、偷窃、造假身份,为了活下去,一切从零开始。可这么做行吗?当一个国家秩序荡然无存之际,社会要如何在这般的混乱中重生?人们要如何在这样一个“他人即恶狼”的“狼性时代”里重建生活?生活秩序的丧失、家庭的四分五裂、饥饿贫困的威胁、战争罪恶感的阴影、对大屠杀的沉默、死里逃生的狂喜——第三帝国的余波持续影响着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度。 本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日常生活文化史及人民精神史,聚焦二战后十年间德国人的战后生活,尤其是其精神心态和情感生活。作者抛弃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和政治框架,从普通人的日常出发:清理废墟的动员,物质匮乏与黑市的经验,及时行乐的追求享受,人口大迁徙的遭遇,女性的自主意识,盟军的再教育,经济起飞的奇迹,“重塑思想”的文化政策,艺术和设计风尚的变迁,以及日常生活中德国人如何集体回避战争的罪责感。战后德国大众生活混乱失序中充满了多重面向,人们既有对战争的悲伤和自怜,又有立刻重新出发的求生欲,有为了生存下来的不择手段,也有劫后余生、渴望生命的及时行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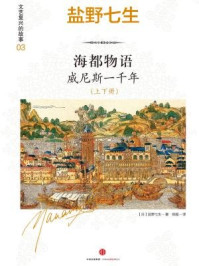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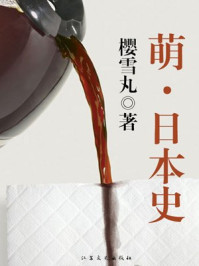
1945-1955年,二战余温未冷的十年,作为罪魁祸首、罪有应得的战败国,它的社会面貌该是怎样的颓废怅惘不知所措,它的重建融合又该历经何等的痛苦撕裂和不安,然而,当我读完这本《狼性时代》我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身为群体中的一员,他们面对亲手摧毁的一切,被末日和希望交织催生出的狂热,在理智抉择和自保本性中,在自我认知和外界评价中,在民族自信和彻底否定中,在现实、未来和历史中,开辟出一条逻辑自洽的辩证认知观,“如果联邦政府坚定不移地让过去成为过去,坚信许多人从主观而言不曾犯下严重罪行的话,那么它在另一方面也会坚定不移地吸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来面对那些动摇国家生存的人。”这本书,始自“零点时刻”,它是主观的,尽管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定义,但客观上总是有某种象征,就像指针无声的划过数字,国家暴力戛然而止,旧的一天过去了,尽管它仍带着旧日的惯性,但零点总是代表新生。城市满目疮痍,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首先从清除瓦砾开始,德国妇女作为主力,以智慧和重体力劳动者形象参与到城市重建,参与感塑造了成就感,从而激发出自信和自我认同,生活困苦、秩序紊乱都不能让她们退缩,音乐、舞蹈和操持生计、黑市交易并行,都是女人们自由快乐的象征。而回归的男人们,固然经历耻辱带着伤痛,他们带着昔日“家主”的认知,期望家庭和社会温柔宽容的关爱,却发现在没有他们的日子里,女人们凭借韧性、适应性和智慧手段,让家庭和社会都能平稳运转,男人们不但没有获得预想的来自家庭下层的呵护供养,反而成为被女人孩子嫌弃的多余,男人竟然要女人们竞争。可惜的是,随着男人们重新掌权,在性别失衡的环境中,男人成为女性的争抢对象,女人们昙花一现的社会性逐步淡化。“战争如同一架巨大的移居、驱逐和劫持机器,将每个幸存者随意抛在某个远离故土的角落。”四千万被迫移居的人,经历过身心摧残后,还要面对选择定居地的难题,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民族、习俗、接纳、融入等一系列考验,过程当然是千难万难,但生活自有其强劲的智慧,无论本地居民对外来者如何排斥,固化的本土文化不可避免的被外来习俗吸引影响,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属于所有人的文化圈层。至于艺术的、物质的、爱的层面,德国人则历经自我否定、文化复兴、投身盟军、彷徨迷茫,直到主动探索。而各盟军各占区的纷争,是意识形态世界在抢占高地,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人都是活在自己的认知里。“广泛的冷漠、普遍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