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游戏的终结
- 新经典 | 胡里奥·科塔萨尔
- 8.7万字
- 小说

内容简介:几乎在他这一生住过的所有宾馆中,房间里总会有一扇封死的门。曾经有人从门里进出过。有人敲过它、虚掩过它,赋予它某种生命力。而在这夜深时分,门后的一切都醒着,都在沉默之中清醒着、渴盼着。·在这日夜交替时分wei一真实的东西,却用令人无法忍受的谎言欺骗着我们。一切都寻常得可怕。·男人津津有味地读着书里的谋杀情节,却被小说中的杀手投射而来的目光灼烧了后颈;生命轮回究竟是苦难的无望重复,还是无知的永恒庇护;在电影院里不经意窥见的乐队演奏,是伪装成假象的假象,也是高于真相的真相;纯真的爱恋化作朝举向天的手指,终结一切嫉妒、温柔与幸福的可能……本卷收录《公园续幕》《一朵黄花》《夜,仰面朝天》等名篇,既延续了科塔萨尔早期短篇小说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奇崛玄妙的文本结构,又呈现了他对人性与命运更深切的审视与悲悯,是科塔萨尔从其美学阶段步入形而上学阶段的重要转型期的代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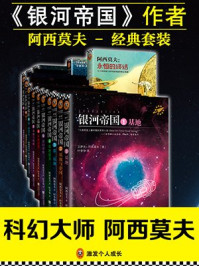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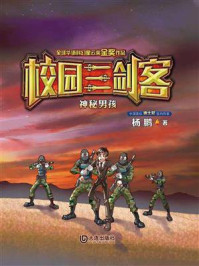
精妙巧思的中篇集。内容奇,构思巧,韵味长。称得上科萨塔尔的代表文集。
小说的高境界,故事性太强只能是一个故事。而这本书,我看见了无数个自己。
在循环的绞索中,阿根廷的黄昏永不落幕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潮湿的黄昏里,科塔萨尔用文字搭建起一座永动的迷宫。那些在铁轨旁摆出雕像姿势的少女,那些在河水中溺亡又重生的倒影,那些在梦境与现实夹缝中游走的角色,共同编织成一张布满倒刺的网。当读者试图抓住某个确切的意象时,科塔萨尔早已将叙事之绳系在阿根廷黄昏的铜钟上,让所有关于暴力、身份与记忆的叩问,在循环的齿轮中永恒转动。 一、身份迷宫里的永动循环 在《美西螈》的玻璃缸前,少年与两栖动物的对视构成了最精妙的身份置换。当观察者的视网膜上倒映出美西螈的瞳孔时,这种主客体的倒错不再停留于卡夫卡式的变形记,而是演化成量子纠缠般的共生关系。科塔萨尔让文字在显微镜与万花筒之间滑动,使读者在显微镜下看见的不仅是细胞分裂的轨迹,更是整个拉丁美洲身份认同的裂变过程——殖民者的剑刃与土著的骨笛在文字的显影液中漂浮,最终都溶解成《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偶像》中那些被月光浸泡的石像。 《公园序幕》的嵌套结构犹如博尔赫斯式的时间回廊,但科塔萨尔在此注入了阿根廷特有的狂欢节基因。当读者发现自己是他人故事中的谋杀目标时,这种叙事诡计已超越单纯的文学游戏,成为对拉美集体记忆的隐喻:每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黄昏,街角咖啡馆里的闲谈都可能成为某个未被记载的暴动序曲,每个人都是他人命运剧场的临时演员。 二、暴力剧场中的集体谵妄 《一朵黄花》中那个执着于转世寓言的男人,像极了马尔克斯笔下的奥雷里亚诺上校在制作小金鱼。但科塔萨尔将这种魔幻现实推向了更锋利的极端:当男孩的尸体最终成为黄色花朵的养料,叙事者那句"虚无就是再也没有一朵黄花开给后来的人看",道破了拉美暴力循环的本质——历史不是线性的进程,而是不断重演的献祭仪式。那些在《迈那德斯之夜》中狂欢的酒神信徒,与现实中涌向总统府的示威人群,在科塔萨尔的笔下共享着同一种迷狂的血脉。 《暗门》里平行时空的交错,恰似阿根廷知识分子在独裁统治下的生存困境。当主人公发现自己的书房通向另一个时空的审讯室,这种空间折叠的恐怖远不及精神分裂的真实。科塔萨尔在此揭露的,是整个民族在历史暴力下的认知困境:我们既是暴力的施加者,又是其承受者,这种双重身份如同探戈舞步中的进退,在《乐队》的乐谱里化作荒诞的休止符。 三、黄昏时分的永恒复调 《游戏的终结》中少女们用身体构筑的雕像王国,是科塔萨尔献给青春的安魂曲。当莱蒂希亚说